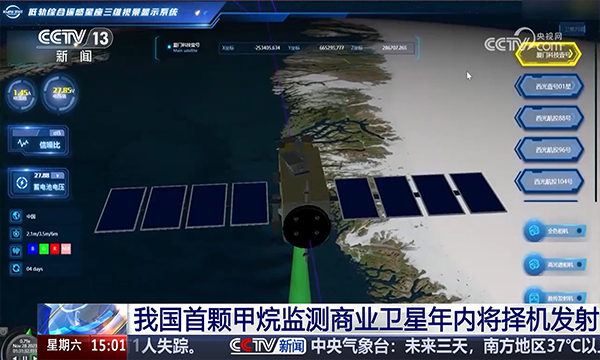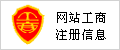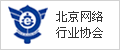煤电环保改造需要巨大的成本投入。所以,为了调动电厂环保改造积极性,国家相继出台了脱硫、脱硝、除尘等电价补贴。近年来,随着排放标准趋严,环保电价补贴标准也相应调高,因为排放标准越严,意味着改造成本越高。
目前我国煤电厂执行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已经是“史上最严”、“世界最严”。奇怪的是,近期不少发电企业却主动请缨、自我加压,要做到“燃机排放标准”或者“近零排放”等。这到底意欲何为?“燃机排放标准”比燃煤发电的排放标准真的更严吗?“近零排放”是环保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要达到真正的“近零”要求,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并增加运行成本,又到底值不值?
在“近零排放”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和发电企业主动或被动的推广开来的时候,本文对此明确地说出了“不”。《中国能源报》本期推出此文,希望给读者提供更多的角度和信息,来审视、品评当下的煤电“近零排放”。
近一年多来,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近零排放”已成为能源、电力、环境、科技甚至社会上的热点话题。部分电力企业争先恐后为自己企业的机组“首先”、“率先”、“第一个”、“首台”实现了“近零排放”、“比燃机排放还低”(本文的“燃机”特指“以气体为燃料的燃气轮机组”,因为它比以液体为燃料的燃气轮机组环保要求高)、“超洁净排放”等报喜。某些新建电厂已按“近零排放”进行建设,为数不少的现役燃煤机组已列入“近零排放”改造计划,科研管理部门抓紧攻关、环保产业界紧紧跟进、媒体持续跟踪、专家学者纷纷解读、宏观经济调控部门也正在研究是否把“近零排放”纳入到宏观决策之中……
一时间,“近零排放”建设或者改造之风,正由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山西、陕西、四川等省市向全国漫延。然而,不论“近零排放”之声多么美妙,伴随着“近零排放”推进过程中的困惑也越来越多,那就让我们试着拨开这些团团迷雾。
1、对“近零排放”概念存在的
若干糊涂认识
(1)“近零排放”的概念不清,一般是以“燃机排放标准”作为判据,对排放标准的表面化错误理解造成荒谬的结果
国内外并没有公认的燃煤电厂大气污染物“近零排放”的定义,实际应用中多种表述共存,如“近零排放”、“趋零排放”、“超低排放”、“超净排放”、“超洁净排放”、“低于燃机排放标准排放”等等。从各种表述和案例中分析得出的共同特点,是把燃煤电厂排放的烟尘、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三项大气污染物(未包含二氧化碳等)与《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23-2011)(以下简称“排放标准”)中规定的燃机要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以下简称“特别排放限值”)相比较,将达到或者低于燃机排放限值的情况称为燃煤机组的“近零排放”。
在“标准”中,根据燃煤机组是“新建锅炉”还是“现有锅炉”、是否为W火焰炉、循环流化床锅炉、是否位于高硫煤省份(广西壮族自治区、四川、重庆、贵州)的不同情况,以及是否位于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划定的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地区,提出不同档次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如,烟尘排放限值为30、20、5mg/m3,二氧化硫排放限值分为400、200、100、50、35 mg/m3,氮氧化物(以二氧化氮计)分为200、100、50 mg/m3。“近零排放”就是要使燃煤电厂排放的污染物,在“表面上”达到或低于最严档的燃机特别排放限值的要求,即烟尘5 mg/m3、二氧化硫35 mg/m3、氮氧化物50mg/m3。然而,从以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也只是表面化的严格。
我国火电厂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限值是采用“浓度”来表示的,因此,“达标排放”是指烟气中的污染物浓度不超过标准规定的浓度限值。由于污染物的“浓度”是由污染物的质量和烟气体积两个因素构成,烟气中的氧含量越高,说明燃烧过程中过剩空气越多,污染物浓度就越低。为防止用空气稀释浓度达标的现象,“排放标准”规定了用“基准含氧量”折算的方法。“基准含氧量”是根据典型的燃料和典型的燃烧技术来规定的,规定燃煤锅炉为6%、燃气轮机为15%。
经粗略换算,可以理解为在典型情况下,燃煤锅炉燃烧所用的实际空气量是理论空气量的1.4倍(也即空气过剩系数α=1.4),而燃气轮机所用的实际空气是理论空气的3.5倍(α=3.5)。虽然在实际工作中不论燃煤还是燃机,往往都是非典型情况,所以都必须要以各自的“基准含氧量”进行折算,但由于“基准”本身就不同,折算后的污染物浓度也是不可直接相比的。如果将燃机和燃煤的排放限制按相同“基准含氧量”折算的话,燃机排放限值的数值是原来值的2.5倍,即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限值分别由5、35、50 mg/m3,变为12.5 mg/m3、87.5 mg/m3、125 mg/m3。换句话说,除了燃机的烟尘的排放限值稍低于燃煤烟气的特别排放限值外,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反而更宽松,将三项污染物合起来计算,燃机比燃煤排放限值要宽松32.4%。这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更严的燃机排放限值实则不然的原因。
再从排放总量看,经测算,典型300MW燃煤锅炉(标态烟气量100万m3/h,空气过剩系数α=1.3),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分别按5、35、50 mg/m3排放时,每小时排放量分别大约为5.4、37.8、54 千克;而300MW级燃机(标态烟气量185万m3/h,空气过剩系数α=3.5),依排放限值要求每小时可以排放9.25、64.25、92.5千克,可见,每小时燃机排放总量是燃煤排放的1.7倍。显然,这样的“近零排放”的要求是荒谬的。
还有,燃机的烟囱一般在80米且不会超过百米,而煤电机组的烟囱一般为180、210、240米,同等排放量由于烟羽抬升高度和扩散条件的不同,燃煤机组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要远低于燃机。
但是,燃机排放限值宽于燃煤排放限值,并不能说明燃机排放标准比燃煤机组排放标准要宽,因为“限值”只是数字大小的比较,而“标准”是“价值”内涵的比较。对火电厂污染控制而言,排放标准的宽严只能用同类发电技术和相匹配的污染控制技术是否达到了最佳技术、经济条件来衡量。这也是“排放标准”为何要划分不同档次的原因。同世界各国一样,我国《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都明确规定,污染物排放标准是依据环境质量标准和国家的技术、经济条件制定的。美国、欧盟等制定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所依据的技术原则为“最佳可行技术”(BAT)。因此,不论是燃机还是燃煤机组,科学合理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与最佳可行技术是相一致的,而且排放限值的大小也是随着技术、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如,我国从1973年《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对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有要求以来,1991年、1996年、2003年、2011年已经多次修订。由于不同地区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不同,技术、经济条件也有所不同,我国法律规定了地方政府可以制定严于国家排放标准要求的地方排放标准,况且2011的“排放标准”中提出了重点地区执行特别排放限值的新规定。
燃气用于民用的环保性能和便捷性要远远优于直接燃煤,而煤炭集中发电的优越性大大优于散烧煤。所以,不同品种的能源应当担当不同的功能,采用不同的排放标准,如果硬要把燃机排放标准当成燃煤电厂的“近零排放”来衡量,就是要驴当战马、马拉磨。
(2)烟气连续监测技术难以支撑“近零排放”监测数据的准确性,用日平均浓度或者多日平均浓度的监测数据与排放限值直接比较是概念性错误,运行时间不足也难以证明“近零排放”系统的稳定性
根据环保部颁布的《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HJ/T75-2007) 中“7.4参比方法验收技术指标要求”规定:烟尘浓度小于50mg/m3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5 mg/m3;二氧化硫浓度等于或低于57mg/m3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7mg/m3;氮氧化物小于或等于41mg/m3时,绝对误差不超过12mg/m3。再根据环保部《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629-2011)、《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非分散红外吸收法》(HJ692-2014)、《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693-2014),二氧化硫的测定下限10mg/m3;一氧化氮(以NO2计)和二氧化氮的测定下限12mg/m3。一些试点项目的监测值低于测定下限甚至低于检出限,结果的可靠性值得怀疑。而这只是测定方法误差而不是自动监测系统的全部误差。如果考虑到监测仪器装设断面和监测点选取的误差,尤其是对于老厂改造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监测断面选取很难做到按技术规范的要求,考虑烟气中含湿量(水分)、温度、含氧量等因素,尤其是湿度的影响对监测精度也会产生较大影响,监测系统的总误差要大大高于分析测定方法的误差。
因此,在客观上和技术上,现有监测手段不支持“近零排放”,说的更清楚一点“近零排放”的监测数据是不可信的。
另外,一些电厂的“近零排放”的数据是以日平均浓度或者多日平均浓度与排放标准中的限值进行比较的,这种比较是概念性错误。我国的污染物浓度排放标准从产生以来,一直坚持“任何时候”不能超标的准则(尽管我一直认为这个准则对常规污染物来说是不科学的,会付出过多的经济代价,但它目前仍然是强制性要求)。“任何时候”不超标一般是指无论长期监测还是随意监测中,任何一个小时的平均浓度都不超过标准规定限值,而不是用日平均或者多日均值与标准比较看是否超标。
同时,为了保障机组波动运行和遇到各种不利情况下企业仍然能够不超标,电厂在环保设施招标、设计、建设时都要保留一定裕度。由于特别放限值本身的数值已经很低,加上留有的裕度,很多实际运行中的机组能到达“近零排放”的要求。如,外高桥三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尽管没有按近零排放设计,但因煤质好、裕量大等因素,基本达到了近零排放。所以目前的“近零排放”也只能说是满足了特别排放限值要求。
由于典型火电厂的脱硝、除尘、脱硫设备是依次串联在烟道上的,影响某种污染治理设备的治理效果不仅取决于设备自身,而且取决于上下游设备的情况。如上游的脱硝会影响到下游的除尘和脱硫,下游的设备状况也会影响到上游的烟气流场,加之机组负荷调整、煤质变化等各种因素都会对烟气脱硫系统产生较大影响。要想长期保持在“近零排放”状态,至少需要一年以上各种可能条件的考验,而现在并没有这么长时间的实践证明。因此,即便“近零排放”监测的数据不是以折算后的燃机标准相比,这样的结果也是不可信的。
(3)“近零排放”在技术上并没有重大创新,且严苛的条件并非一般燃煤电厂都能达到
我国环保产业界特别是为燃煤电厂直接服务的主流环保产业界,在强力环保要求下火电厂不断进行的大气污染控制设备建设和改造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使我国火电厂污染控制水平总体达到了国际先进,一些电力企业自身通过技术创新,也实现了世界领先的节能减排成效。
在“近零排放”方面,环保产业界在强大的机遇和压力下迎难而上,加强了技术创新力度和提高了服务水平,这也都是值得尊敬和赞赏的。但是,大型燃煤电厂大气污染控制所采用的除尘、脱硫、脱硝主流技术和主体工艺、设备,近几十年来并没有重大突破,世界范围内基本上都是采用上世纪中后期开发的成熟技术。从已经“实现”“近零排放”所采用的技术看,主要是对已有技术和设备潜力(或者裕量)的挖掘、辅机的改造、系统优化、大马拉小车式的设备扩容量、材料的改进、昂贵设备的使用等。如,除尘要采用的湿式电除尘器已在我国冶金等行业有广泛应用,但在电力行业,除了日本个别电厂采用之外,并不是普遍采用;二氧化硫控制采用的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主要是增加系统的裕度和复杂度,如原来脱硫吸收塔喷淋层为3层,现改为5层或者增加一个吸收塔;氮氧化物控制仍采用常规选择性催化还原法,但是增加了催化剂用量。这从达到“近零排放”的其他条件也可以看出一些规律。如,要求煤质含硫量低、灰份较低、挥发份高、低位发热量高、机组负荷运行相对平稳等实现“近零排放”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条件对于中国目前平均含硫量超过1%、灰份近30%、以及大量低挥发份的电煤来讲,即便是实现特别排放限值都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虽然大量的小的创新都是实实在在的创新,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总体来说,主要还是常规技术外延的扩大,不是重大和突破性创新。非创新驱动的“近零排放”,必然逃脱不出以过高的投资和运行成本实现很低的减排量目标,使污染物减排边际成本呈指数式增长的规律。
(4)“近零排放”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投入产出比太低
不论是从现有的环保技术进展来看,还是从二十多年前的环保技术来看,如果不考虑成本的话,理论上都是可以做到真正的“近零排放”。因此,从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来评价污染控制技术选择是否正确,是环境经济管理的核心,也是“近零排放”能否大面积实施的关键。
首先看环境效益。环境效益可以从排放总量减少和环境质量改善两个方面来分析。假设两台600MW机组,在燃用优质煤的条件下(灰分约10%、硫含量约0.8%、挥发份约30%),并采用了低氮燃烧方式,锅炉出口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浓度分别为15g/m3、200 mg/m3、300mg/m3,按特别排放限值要求,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在分别达到20、50、100 mg/m3时,每小时脱除量约为65912、8580、880千克,合计脱除75372千克,对应的脱除效率分别为99.7%、97.5%、66.7%。可见,两台600MW机组,即便是在折算为6%含氧量时,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分别达到5、35、50 mg/m3时,排放量每小时可再减少约66千克、66千克、220千克,合计352千克。“近零排放”比起特别排放限值要求,三项污染物合计可多脱除0.47个百分点。考虑到电厂高架源排放对环境影响要小的特点,多脱除的部分对环境质量改善作用轻微。
再看经济效益。主要用单位污染治理成本与全社会平均污染治理成本的大小来分析。仍以两台60万千瓦机组为例,目前脱除三项污染物的综合环保电价为2.7分/kWh,从不同电厂的测算情况看,实现“近零排放”的环保成本在原有电价的基础上增加1~2分/kWh,则增加的352千克污染物削减增量的成本达到1.2-2.4万元/h。粗略估算多脱除的污染物平均成本为34-68元/kg,远高于全社会平均治理成本(按制定排污收费标准时测算的全社会平均成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约为1.26元/kg)。
最后看综合效益。主要从环保系统对资源、能源消耗方面和对机组的可靠性影响方面进行分析。“近零排放”增加了更多的环保设备,系统阻力增大,能耗水平提高,设施整体技术可靠性降低。如,脱硫设施需要设计更多层的吸收塔喷淋层甚至需要吸收塔串联或并联,脱硝设施需加装三层催化剂甚至在炉内再加装SNCR,除尘方面必须加装湿式电除尘器等。
从以上三个效益分析来看是得不偿失,甚至是劳民伤财。
2、企业为什么要
主动开展“近零排放”
近一二年,电力企业对执行世界最严的《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中存在的标准过严难以达标的问题,以及要求出台相关经济政策等方面都有强烈诉求。而且随着雾霾问题的严重,国家进一步加大了污染控制的力度,特别排放限值提前实施,要求电力加快治理步伐,而很多企业一直苦于难以选择合适的技术路线,难以在2014年7月1日最后期限仍难达到排放标准要求。
在国家有关部门对电力排放的监管中,一部分机组因不能满足环保要求被通报限期改正。但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为什么一部分电力企业又“主动”提出了比特别排放限值更严要求的“近零排放”呢?
虽然我们不用怀疑企业对环保贡献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但我们更不应抛开科学机制去完全相信企业环保主动性,如果这样,就不需要环保法规的约束,就不需要政府的监管,甚至不需要推进市场经济。
但是,为什么“近零排放”的运动是由企业挑起而不是政府发起?
当我们认真追寻某些企业为什么要“近零排放”的动因时,就会发现一些规律。有的是为了获得对企业当前或者未来发展有利的新的煤电项目的审批,有的是为了现有煤电的生存,以防止过度关停还处于“青壮年”且有良好效益的煤电机组,有的是害怕政府让企业实施燃气替代煤电从而付出比“近零排放”高出约数十倍的成本,还有的是因为种种原因与地方政府达成某种协议。
但始料不及的是,企业的这种“战术”在环保产业界、媒体、专家的共同热捧下,在部分地方政府的行政要求下,逐步演变成了企业主动或者是被动但表现出的是争先恐后搞“近零排放”的局面。这种“正反馈”式的机制,使中国正上演着一场让全世界为之瞠目结舌的火电厂“近零排放”“大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