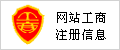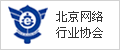摘要 上 利用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应采用质押而非抵押方式。碳排放权是权利人对碳配额或碳信用所表征的容许碳排放量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排除他人不法干涉的权利,其性质为准物权。允许碳排放权质押,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践中是必要的。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的制定中,应衔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的规定,明确碳排放权的适质性,并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确立其在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的质押公示方式,从而为金融机构开展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业务提供法律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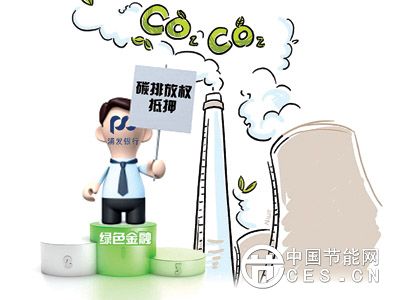
从2013年起,我国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广东、湖北和深圳等七省(市)陆续启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以期通过交易手段推进温室气体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与此同时,部分试点省(市)商业银行开始开展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业务,向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企业提供授信支持。但是,由于法律层面对碳排放权此种新型权利的相关规定付诸阙如,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业务开展的深度与广度受到严重制约。实践中面临的问题,亟须理论与立法的考量和回应。
一、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发展状况
(一)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缘起
碳排放权担保融资是在为推进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而实施碳排放权交易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20世纪末,因过量人为温室气体排放肇致的气候变化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1997年《京都议定书》创造性地引入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即将排放温室气体界定为一种以碳配额(Allowance)或碳信用(Credit)为凭证的量化权利,进而通过碳配额或碳信用的交易为碳排放主体创造减排经济诱因,促使其减少排放。
碳排放权交易有总量控制与交易(Cap-and-trade)和基线与信用交易(Baseline-and-credit)之分。[1]在总量控制与交易中,首先确定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Cap),然后将该总量分解为若干份配额(Allowance)分配给相关排放源。配额为碳排放权的凭证,排放源排放温室气体必须有相应数量的配额冲抵。如果排放源实际排放的温室气体量超出了其排放配额所允许排放量,则必须另行购买相应配额冲抵超排的部分,否则将受重罚;反之,如果排放源实际排放的温室气体量少于其排放配额所允许排放的量,多余的配额可以出售获利(Trade)。如此,通过总量控制形成的减排压力和权利交易形成的利益诱导,可有效激励排放源采取减排措施。在基线与信用型交易中,不设置允许排放的总量,而是为排放源设定一条排放率或减排技术标准基准线(Baseline),再根据排放源减排后优于基准线的部分核发减排信用(Credit),由无法完成减排目标的排放源购买。同总量控制与交易一样,基线与信用交易也能创造经济诱因,推动排放源实施温室气体减排。在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下,总量控制确定所有排放源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赋予减排以刚性;权利交易允许排放源根据经济成本自主选择是自行减排还是通过购买排放权达到减排目标,赋予减排以柔性。因此,碳排放权交易兼具原则性与灵活性,兼顾经济效果与环境效果,是较为理想的减排手段。
《京都议定书》引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后,欧盟通过第2003/87/EC号指令,决定设立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mission Trade System, EUETS)。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自设立以来,发展极为迅速,减排效果也十分可观,欧盟2009年在1990年排放水平上实现温室气体减排17.4%,与《京都议定书》其他众多缔约方减排实效不彰形成鲜明对比。[2]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和世界上负责任的大国,我国积极探索通过交易方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011年3月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2011年10月,北京、天津、上海等七省(市)获准在“十二五”期间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并于2013年陆续启动交易。在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中,试点企业有以所获取的碳排放权作为担保向银行融资的需求,部分商业银行基于碳排放权交易广阔的发展前景、推动绿色信贷业务发展、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等多重考虑,也愿意接受碳排放权作为担保给予企业授信,从而使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发生成为可能。
(二)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现状
2014年9月,湖北宜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210万吨碳排放配额作质押,获得兴业银行4000万元贷款,成为国内首笔碳配额质押贷款业务。[3]2014年12月,华电新能源技术开发公司在广东省以碳排放配额作抵押获得浦发银行1000万元融资授信,成为国内首笔碳配额抵押融资业务。[4]随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银行等其他商业银行陆续推出以碳排放权作为担保的信贷产品,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业务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在实践中,以碳排放权作担保融资多被称为“碳排放权质押”,也有少数被称为“碳排放权抵押”。在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中,质押与抵押是两类不同的担保方式,适用不同的法律规则。以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究竟是采用“质押”还是“抵押”方式,亟须明确。抵押与质押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担保品设定抵押后不影响担保人对担保品的使用,而质押则不然。如房屋抵押后不影响所有权人使用房屋,动产质押后所有权人不能使用质物。碳排放权的作用在于冲抵碳排放量,并且一经冲抵权利便告消灭。若权利人以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后仍可使用碳排放权,则担保权人的权利毫无保障可言,因此以碳排放权作为担保不应属于抵押。此外,从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看,只有以建设用地使用权等不动产权利设定担保才称为抵押,以其他权利设定担保均称为质押。故统一确定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方式为质押较为适宜。本文所称碳排放权担保融资,指以碳排放权作为质押进行融资。
目前,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新型权利,其内容、性质、效力如何,在理论上存有争议,在法律法规中也未明确。商业银行接受一种在法律上不清不楚的权利作为融资担保,难免会顾虑重重而逡巡不前。我国《物权法》第五条规定了“物权法定”原则,即物权的种类和内容由法律规定,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创设,但在《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确立的可供质押的权利范围中没有明确规定碳排放权。开展碳排放权质押融资的法律依据不明确、不充分,使得即使有部分商业银行敢于先行先试接受碳排放权作为融资担保,也难以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大规模普及。以碳排放权进行质押,理论上是否可行,实践中有无必要,都是将来碳排放权交易立法无法回避的议题。
二、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理论分析
(一)碳排放权的法理含义
概念界定是理论研究展开的基点,对碳排放权质押的研究也是如此。目前在实践中将碳排放权理解为排放一定量温室气体的权利固然没错,但这一实践中的界定没有清晰揭示出碳排放权的构成要素,尚未在深层次把握碳排放权的内涵,因而无法作为碳排放权的理论定义,也难以为碳排放权质押的制度设计提供有效的理论支撑。遵循概念法学的研究进路,欲明晰碳排放权的法理含义,须先厘清权利的客体、主体、内容等权利构成要素,这三者之中又以客体最为根本,因为法律在不同的客体之上设定权利,就须依据不同客体的不同状况合理设计权利内容和保护方法,从而使权利客体可以将一权利区别于其他权利。[5]一般认为,权利客体是权利人所享有之权利与义务人所承担之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6]此处所指对象,种类颇为复杂,既可以是有体的事物,也可以是无体的事物;既可以是事实存在的事物,也可以是制度构建的事物。[7]
本文认为,碳排放权的客体为容许碳排放量(Allowable Carbon Emission Volume)。所谓容许碳排放量,是指在一定时间和地域范围内,经由法律规定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限量,是通过法律技术人为创造的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稀缺制度资源。容许碳排放量由“存量”与“增量”两部分构成。存量是指在不考虑从大气中消除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减排项目的情况下,所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在总量控制与交易中,所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就是容许碳排放量的存量。容许碳排放量的存量是由法律拟制产生的无形之物,为便利权利人行使权利,需要赋予此种无形之物以外在有形的表征,这种有形表征就是碳配额。增量是指在存量之外,通过人为实施从大气中消除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减排项目所额外创造的容许碳排放量。在基线与信用型交易中,通过减排项目所减少的温室气体数量就是容许碳排放量的增量。容许碳排放量的增量同样是由法律拟制产生的无形之物,这种无形之物的外在表征就是碳信用。例如,某地进行总量控制,确定某一年度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限量为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这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就是容许碳排放量的存量,以碳配额为外在表征。该地通过建设造林固碳项目,从大气中清除了100万吨二氧化碳,则其允许排放的二氧化碳相应增加100万吨,这增加允许的1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就是容许碳排放量的增量,以碳信用为外在表征。
在实践操作中,容许碳排放量被等量划分为若干基本单位,每一基本单位代表排放一吨二氧化碳当量温室气体的权利,并以一个碳配额或碳信用表征。每个碳配额与碳信用都有唯一的序列号区别彼此,从而使被碳配额与碳信用所表征的每单位容许碳排放量具有独立性与特定性,进而有了可被支配的可能性。碳排放权权利人拥有多少碳排放权,体现为其在碳排放权交易系统的账户中拥有多少碳配额或碳信用;权利人行使碳排放权,表现为其利用碳配额或碳信用冲抵自身的碳排放量,或者将碳配额或碳信用转让给他人。权利人以外的其他人负有不妨害权利人占有与利用碳配额或碳信用的不作为义务,如不得侵人系统盗窃权利人的碳配额或碳信用。由此可见,权利人的权利与义务人的义务所指向均为碳配额或碳信用,实质是指向碳配额或碳信用所表征的容许碳排放量,故容许碳排放量是碳排放权的权利客体。其实,碳配额、碳信用只是来源不同,并无本质区别,二者之于容许碳排放量,与股票之于股份无异。
碳排放权的主体,是指碳排放权所蕴含利益的享有者,亦即具有支配碳排放权客体法律资格的人。碳排放权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和符合条件的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等其他法律主体在一定条件下也可成为碳排放权的主体。碳排放权的内容,体现为权利人为实现其利益而,可对容许碳排放量所施加的影响,具体表现在积极权能与消极权能两个面向。从积极权能的一面看,权利人为实现碳排放权,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对容许碳排放量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对容许碳排放量进行占有、使用、收益与处分,如使用碳配额或碳信用冲抵自身碳排放量或者以碳配额或碳信用质押;从消极权能的一面看,权利人得排斥并去除他人对容许碳排放量的不法侵夺、干扰与妨害,如在碳配额或碳信用被他人非法侵夺或干扰、妨害的情况下,权利人可凭借碳排放权的消极权能排除他人的不法干涉,回复其权利的圆满状态。综上,碳排放权可界定为权利人对碳配额或碳信用所表征的容许碳排放量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排除他人不法干涉的权利。
(二)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可行性分析
从法学理论和我国《物权法》的相关规定看,权利质权的标的是所有权和不动产用益物权以外的可转让财产权利。[8]因此,要从理论上论证碳排放权具有适质性,应说明碳排放权符合三项要件:第一,碳排放权为财产权利;第二,碳排放权具有可转让性;第三,碳排放权非所有权和不动产用益物权。
1.碳排放权为可转让的财产权利。尽管古往今来对财产权的概念存在诸多见解,但财产权从本质而言是人身权以外具有经济价值的权利。[9]碳排放权产生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权利交易形成利益诱导机制,促使温室气体排放源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因此碳排放权必须是具有经济价值的非专属性权利,在法律上定性为可转让的财产权利应无疑义。但吊诡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碳排放权交易法案明确宣示碳排放权并非财产权。[10]这又是为何?其实,这是立法者的无奈之举,并非碳排放权不符合财产权的权利特征所致。
一般说来,立法者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总量控制方有碳排放权的产生,但恰当确定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殊非易事。在进行总量控制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环境保护的要求,也要考虑经济合理性和技术可行性。若确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过于严格,将导致市场中碳排放权过分稀缺,价格过高,给企业增加过多的生产成本,对经济发展的冲击过大;反之,如确定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过于宽松,将导致市场中碳排放权供过于求,价格过低,企业缺乏减排的经济动力,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减排效果难以实现。由于立法者的有限理性和经验不足,在碳排放权交易立法之初,其很难合理确定允许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而是必须在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对碳排放权的数量进行适当调整,在市场中的碳排放权供过于求时,收回部分碳排放权,将碳排放权的供求维持在合理水平,保障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顺畅运行。但是,一旦将碳排放权确定为财产权,国家为调节市场中的碳排放权数量,从企业收回碳排放权就面临合宪性的难题。根据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Due Process Clause),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未经正当程序不得被剥夺;根据该修正案中的征收条款(Takings Clause),政府只有在为公共使用的目的,并经合理补偿的情况下,才有权力征收私人财产。据此规定,国家要收回碳排放权,一方面,要经过严格且冗长的正当法律程序,给国家调节碳排放权的数量造成掣肘和时间上的迁延;另一方面,合理补偿的要求也给国家造成一定经济负担,尤其在碳排放权免费分配给私主体的情况下,有偿收回更是得不偿失。为了规避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给调节碳排放权数量造成的麻烦,立法者索性规定碳排放权不是财产权,从而无美国《宪法》适用之余地。从理论层面而言,碳排放权完全符合财产权的特征,美国立法将碳排放权定性为非财产权在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为解决实践中的问题而罔顾理论上的合理性,此举充分说明了美国立法者秉持的实用主义态度。因此,美国的立法不足以成为否定碳排放权具有财产权属性的充分依据。
2.碳排放权非属所有权或不动产用益物权。确认碳排放权为可转让的财产权利后,仍需进一步考量碳排放权是否为所有权或不动产用益物权。要回答这一问题,须首先澄清碳排放权的法律性质。本文认为,在大陆法系物债二分的财产权结构中,碳排放权目前合适的定性应为“准物权”。准物权意指在物权法所规定的典型物权种类之外,性质与要件等相似于典型物权并准用物权法有关规定的财产权,也就是所谓非典型物权。[11]碳排放权为准物权的第一层含义是碳排放权具有物权的基本特征,因而可以物权化,这具体表现在:其一,碳排放权的客体容许碳排放量虽然无体无形,但借助技术手段可使之符合独立性、特定性、可支配性等物的基本要求;其二,碳排放权体现为对容许碳排放量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具有直接支配性和排他性等物权的基本特性。碳排放权为准物权的第二层含义是碳排放权虽然具有物权的基本特征,但也具有典型物权所不具备的特性,只能是“准”物权而非物权。碳排放权不同于典型物权的特性主要体现在客体的特殊性和某种程度的公权属性两方面。其一,碳排放权的客体容许碳排放量是法律拟制之无体物,典型物权的客体是有体物;其二,碳排放权的行使事涉社会公益,受公法管制较多,具有某些公权色彩,如达到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一定数量以上等门槛条件的温室气体排放源必须取得碳排放权冲抵自身碳排放量,是公法科予温室气体排放者的义务,碳排放权的取得一般须经过行政许可;而典型物权的行使较少涉及社会公益,属意思自治的范畴,私权色彩浓厚。所有权为完全物权,意指权利人对特定的物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从权能看,所有权与碳排放权确有相似之处,但所有权为典型物权,其客体一般为有体物,与作为准物权的碳排放权有着明显区别。同理,因不动产用益物权的客体不动产为有体物的下位概念,同时不动产用益物权为典型私权,故碳排放权亦不同于不动产用益物权。
综上分析,碳排放权完全符合“所有权和不动产用益物权以外的可转让财产权利”这一权利质权标的的基本要求,具有适质性。
(三)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必要性分析
允许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不存在理论障碍,但仍须考察此举的必要性。应当说,允许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不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无论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均具有积极意义。
1.允许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具有微观层面意义。实行碳排放权交易后,碳排放企业必须获取碳排放权冲抵自身碳排放量,富余的碳排放权可以出售获利。因此,碳排放权成为碳排放企业必备的生产要素和重要资产。允许以碳排放权作为担保融资,有利于企业盘活资产存量,提高资产利用效率。
从国外的经验看,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之初,由于交易经验欠缺、制度建设不足等方面的问题,碳排放权的市场价格往往剧烈波动,如在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第一阶段,碳排放权交易开始后的6个月内碳配额的价格翻了三番,到2006年4月最高价格超过30欧元,但随即在一个星期内价格暴跌一半,并在之后的一年中价格降到零点。[12]如果只有碳排放权的买卖交易业务,具有短期融资需求的企业很可能被迫在碳排放权价格低迷时出售碳排放权而蒙受损失。允许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企业可以选择不出售碳排放权而以碳排放权作质押获得资金支持,既解了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又可保留碳排放权,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碳排放权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在微观层面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经济效益。
2.允许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具有宏观层面意义。参与碳排放权交易的主体越多,碳排放权的供给与需求就可能越旺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运作相应也就越繁荣。但是,参与交易的市场主体越多,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管理也就越复杂,尤其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之初,由于市场交易管理规则不尽完善,参与交易的主体过多容易导致市场秩序的紊乱,影响碳排放权交易的成效。为求平衡,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主体往往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扩大。如在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运行的第一阶段(2005—2007年),仅有电力生产、钢铁、造纸等行业的企业参与交易,第二阶段(2008—2012年)航空运输企业开始参与交易,第三阶段(2013—2020年)交易主体范围再扩大至化工、炼铝等行业企业。[13]
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初期,参与交易的市场主体有限导致市场交易不活跃,这使得企业即使能通过减排创造剩余碳排放权,也难以通过市场交易自由变现。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精髓在于通过权利交易创造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推动企业减排,如果企业即使减排也不能通过交易获取经济利益,则必然有损企业减排的积极性,进而从根本上危及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效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展。如若允许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企业即便难以通过市场交易兑现碳排放权的经济价值,也可通过碳排放权的质押获得资金支持,有助于提升企业参与交易和推进减排的积极性。这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立之初,尤其是碳排放权交易试点阶段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允许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在宏观层面有助于保障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取得成效,有利于促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健康发展。
三、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立法实现
前文已述,允许碳排放权担保融资,在理论层面不仅可行,而且必要。但要解决实践中面临的问题,还有赖于立法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在我国推进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立法也提上了主管机关的议事日程。在此时点探讨碳排放权担保融资的立法实现问题,显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明确碳排放权的适质性
《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规定:“债务人或者第三人有权处分的下列权利可以出质:(一)汇票、支票、本票;(二)债券、存款单;(三)仓单、提单;(四)可以转让的基金份额、股权;(五)可以转让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六)应收账款;(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此规定采用“列举+概括”的方式界定了可供质押的权利范围。由于《物权法》立法之时我国尚未试行碳排放权交易,《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列明的可供质押的权利未涵盖碳排放权。目前,要使碳排放权质押得到合法性支持,应衔接《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出质的其他财产权利”的兜底条款,在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中明确碳排放权的适质性。
作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主管机关,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已于2014年12月颁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并在此基础上研究起草行政法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草案)》,准备尽快提交国务院审议,但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中未有涉及碳排放权质押的内容。从推动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碳金融市场发展的角度出发,起草中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应当明确碳排放权的含义及其财产权属性,在立法上认可其适质性,从而与《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相呼应,为目前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业务的开展提供法律依据。
(二)明确碳排放权质押公示方式
基于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物权的设立须以交付或登记等法定方式对外公示,权利质权的设定亦莫能外。《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至第二百二十八条为第二百二十三条列明的各项权利,规定了交付或登记等质押公示方式,但由于碳排放权不在《物权法》第二百二十三条列举的权利之列,碳排放权质押的公式方式需另行考量。从碳排放权的特征看,其与股权有众多相似之处:碳排放权的客体容许碳排放量为无体物,股权的客体股份也为无体物;碳排放权有碳配额或碳信用为权利凭证,股权有股票为权利凭证;在实践中,碳排放权交易与股权交易均可借助电子化交易系统进行。因此,碳排放权质押的公示方式可以参考股权质押的公示方式确立。
《物权法》第二百二十六条规定:“以基金份额、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登记的股权出质的,质权自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五十五条的规定,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是为证券交易提供集中登记、存管与结算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在碳排放权交易中,也存在类似的机构,即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国务院碳交易主管部门负责建立和管理碳排放权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以下称注册登记系统),用于记录排放配额的持有、转移、清缴、注销等相关信息。注册登记系统中的信息是判断排放配额归属的最终依据。”因此,在未来制定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中,可以明确规定以碳排放权出质的,质权自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换言之,以碳排放权出质,质权的设立应采用登记生效主义,登记是质权的生效要件而非对抗要件。从规范角度看,《物权法》关于质权的设立严格坚持了债权形式主义的立法模式,即质权的设立不仅需要当事人的债权合意,还须经过交付或登记的法定形式始能生效。如《物权法》第二百一十条和二百一十二条规定,设立动产质权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质权合同,质权自出质人交付质押财产时设立;第二百二十四条至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各类权利质权自交付权利凭证或办理出质登记时设立。为与《物权法》的既有规定相容,碳排放权质权的设立也应坚持登记生效主义。从实践角度看,因为碳排放权使用与转让均须通过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方能实现,所以坚持登记生效主义,规定由碳排放权注册登记机构办理碳排放权出质登记时质权设立,能够阻止碳排放权人在权利出质后恶意处置碳配额或碳信用,有效保障质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交易安全,合理可行。从法理角度看,质押是通过质权人以占有或登记等方式控制质物给出质人施加压力,以促使其履行债务从而实现债权的,如质权人不能实际控制质物,则质权无法设立,这也是为何不得以占有改定方式设立质权的理由。[14]如碳排放权质押采用登记对抗主义,质权自当事人达成债权合意时即得设立,则此时质权人尚未对质押标的产生有效控制,有违质押制度的运作机理;反之,如碳排放权质押采用登记生效主义,质权自登记时设立,则此时质权人已能有效控制质押标的,与质押制度的运作机理相符。
在《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条例》明确碳排放权的适质性及其质押公示方式后,碳排放权质押的其他事项可适用《物权法》中权利质权的一般规定。由此,现存金融机构开展碳排放权担保融资业务无法可依、无章可循的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作者:夏梓耀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法律事务处)
来源:《金融法苑》总第92辑
主办:北京大学金融法研究中心
主编:洪艳蓉
本辑执行主编:张立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