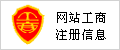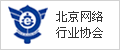2009年9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纽约召开。时任北京环境交易所董事长的我在参加“中美低碳经济峰会”时,面对台下的数百位中外听众,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国际社会是一个大家庭,欧洲、美国等发达地区,经过长期发展,经济和社会形态已经高度成熟,好比五六十岁的老人。他们不干重活,技术先进、能耗很低,70%的排放都来自消费部门。而中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18岁的小伙子,干活多,自然吃的多。然而我们还不太富裕,处在成长发育的过程,吃的是粗粮(以煤为基础),排放自然就高,并且主要集中在工业部门,减排压力和难度远超发达国家。
长期以来,一些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过重的减排责任,这客观上存在很大难度,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发达国家提供相应援助,例如帮助年轻人“改变膳食结构”,提高作业技能等。忽略发达国家由“青壮年劳动力”发展到现阶段所造成的大量排放,一味地要求发展中国家干重活,还不允许增加排放,这在经济规律和道义上都是讲不通的,也不利于解决实际问题。
过去的八年间,国际社会也是通过很多这样积极的碰撞,历经挫折并走向共识,其中一项重要成果是2016年正式生效的《巴黎协定》。然而,国际社会的合作并未如预期中顺利推进。2017年6月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意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引起了世人哗然。在声明中,特朗普把气候变暖归咎于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碳排放,并“组织”出很多数字,例如中国14天的碳排放量可以抵消美国所有的减排成果,《巴黎协定》允许中国新建数百座煤电站,印度煤炭生产加倍,却限制了美国的工业生产,并将打击美国经济、就业和竞争力。他宣称《巴黎协定》会导致2040年美国GDP下降3万亿美元,650万工业工作岗位流失。在当下割裂的美国社会,民粹主义的话音能轻易地将应对气候变化“坐实”为中国抑制美国竞争力而编造的陷阱,并引申出一个看似无法证伪的阴谋论。
一时间国际社会舆论纷纷,联合国秘书长、欧盟、中国等主要领导人,美国各界人士发出一片愤懑和遗憾之声。一个是人均GDP已接近6万美元,服务业占主导且拥有全球最强科技和金融实力的美国,一个是人均GDP才刚刚超过8000美元,工业化、城镇化还在进程中的中国,在减排问题上谁的压力更大,答案不言而喻。因而特朗普这一番言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若认真地用真实数据去回复其所提出的种种质疑,恐怕是未解真味。特朗普本人怕是没有兴趣了解所谓真相的,他所要做的无非是找出些针对发展中国家耸人听闻的数据,调制成煽动民众的借口,树立一个上任即兑现承诺和推崇美国利益的总统形象。

深究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的真正原因,一方面,特朗普政府提振经济和就业的主要手段是复兴制造业和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这客观上需要寻求更低的能源成本和更宽松的环境管制,势必增加化石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因此与国际社会共同制定的气候政策发生冲突。基于此,美国预计很难完成奥巴马政府之前所提出的国家自主贡献,而继续留在《巴黎协定》容易招致美国国内环保团体或地方政府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带来风险和后患,削弱其政策权威性;另一方面,美国共和党保守派向来反对政府采取任何强制性减排措施,他们普遍信奉自由市场理念。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既能为能源集团打破紧箍咒,缓解美国制造业颓势,也有利于特朗普与共和党内保守派搞好关系。
纵观国际社会,责任、权力、义务和收益从来都是对等的。特朗普政府短期内似乎通过兑现竞选承诺而树立了威信,有助于转移目前国内空前的弹劾压力,并获得共和党内的支持。但是长期看势必会削弱美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使美国的大国霸主形象被其“精致的利己主义”蒙上阴影。一定程度上,美国利益至上的表现正是其国际地位衰落的表现,正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美国一己优先和利益至上的诉求,正是其国际影响力和综合国力减退的映射。
只看眼前利益而不顾长远责任,作为昔日老大哥的美国,如今对小伙伴们的“家长里短”失去兴趣,为看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奉行美国利益之上,国内利益优先。如果美国只是独善其身也罢,却还要跳出来阻挠和帮倒忙,不能维护和遵循有关各方达成的积极共识,此项举措毫无疑问是与国际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相违背的。长此以往,不肯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美国,能否对他国维持较强的影响力,对国际秩序保有公信力,话语权,持续发挥自己的软实力,恐怕都将被打上问号。
所以,这场不体面的退出,对追求利益优先的美国来说,短期获益的仅仅是特朗普政府,而美国长期的战略竞争力、国际领导力和影响力必然受损。对于国际社会而言,美国的退出更是对人类联合对抗气候变化的努力的一记重击。16年前,布什政府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导致《议定书》拖延到2005年才生效。这次虽然《巴黎协定》的法律效力不会受到影响,并已于去年的11月4日正式生效,但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的退出必定对协议的实施效果和他国的执行情况造成客观影响。
首先,美国此举会打击其他国家对于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并滋生出更多怀疑论,导致他国减排力度缩水甚至停滞。例如2001年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后,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也相继退出;其次,因为美国的减排不作为,将使得距离2摄氏度升温目标的减排缺口进一步增大,加大其他国家的减排压力;同时,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承诺等将进一步落空。
无论如何,美国人民所选出的这样一位长于商业交易、看重利益变现的总统使美国逐渐放弃道义的制高点,难以再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领袖角色。美国不干了,“接盘”的任务预计将落到了欧盟和中国身上。欧洲固然希望能够接过旗帜,成为新的气候秩序引领者,但从客观上看,欧洲近年来的衰退趋势明显,英国脱欧,难民潮等问题更令其深陷困局,如果美国退出,欧盟扛旗,则意味着全球减排缺口和国际资金缺口将由欧盟承担,这对欧洲显然颇有难度。欧盟能否以呼号天下的底气来力挽气候变化的狂澜,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与此同时,很多评论纷纷倒向中国,认为美国的退出能够帮助中国成为气候战役的领袖,这种说法难免有些不切实际。就像上文谈到的,“尚在长身体中的年轻人”在国际社会的围攻倒逼下,加上国内自身转型升级的压力,现实处境是其不得不减排。
所幸这些年,减排的紧箍咒并没有让我们丧失改革的魄力和信心。通过瘦身健体,减少摄入,提高效率,中国咬着牙坚持履行着减排承诺,尽管这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来说无疑是负重上坡,难上加难,但这并没有撼动我们以改革谋发展的决心。更重要的是,中国自身意识到应对气候变暖,治理环境污染,促进能源高效利用等任务已迫在眉睫,转型升级、节能减排是一件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因而我们推动供给侧改革,确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并且在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力推绿色改革新政,倒逼提质增效,提出2030年碳排放达峰等切实的减排措施,这些举措都使中国在国际气候变化治理新框架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全球治理领域领导力更迭和分化之际,以上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战略机遇和积极因素。当然,我们也应该充分评估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战略定位。中国要实现已经提交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需要付出巨大努力,总投资预计将超过20万亿元,对此我们已经表示要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减排义务。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此举可能意味着更多的减排责任和出资义务,并对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带来挑战,与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与承受能力之间存在差距。主导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绝非易事,我们既要心向往之,也要水到渠成,谋定而后动。
国际社会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也要遵循历史曲折上升的规律。对于美国提出的重新谈判巴黎协定的提议,今天各国都不愿理会,然而从长远现实出发,没有美国的参与,这个关系人类命运发展的重大组织体系是不完整的,是缺乏共识基础的。尽管《巴黎协定》督促世界各国同心协力,提出并贯彻实施国家自我贡献目标,当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在减排问题上存在巨大分歧,逆向冲突的价值导向必然会产生巨大的摩擦从而导致《协定》难以发挥作用。要弥补和缝合分歧,需要时间的冲刷,局势的变迁,历史的机遇和沉淀。终归人类命运还是要由我们自身的共同体而主宰,要包括最主要的力量而凝聚共识和合力。
具体来看,全球气候秩序变迁的重要历史节点,往往与美国国内两党政治气候变化高度相关。《巴黎协定》规定成员国加入3年后才能正式退出,此外还有1年等待期,也就是说美国最快在2020年11月左右才能正式退出,届时正值美国下轮大选,不排除在此期间特朗普政府改变风向,或者两党轮替的可能。当然,新的完整体系气候格局的形成,还要在国际格局和实力较量的过程中,在这种力量的再平衡中实现新的均衡 。FT中文网
(作者系国富资本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