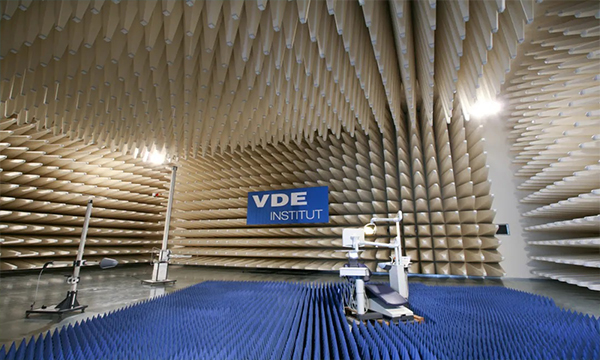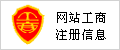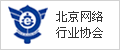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曾36次提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成为对我国现阶段最深刻、最具高度的表述。
“新”,意味着新机遇、新飞跃,也意味着新形势、新挑战。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中,恐怕再也没有比新技术、新发明更“新”的东西了,它们代表人类智识的最前沿,为社会进步提供着最根本的动力。
但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尤其在观念更开放、知识更普及的今天,技术之“新”,与社会之“新”越来越深刻地交织在一起。技术不仅是研究和应用工作,也越来越多地参与着社会意识的演变。
技术在为能源领域带来变革的同时,也一次次带来与社会的善意交锋,在创造着科学与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创造着社会与文化价值,成为整个社会进步的"新动能"。
“激荡”特高压
2017年9月1日,十九大开幕前的一个多月,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巴西总统特梅尔的共同见证下,巴西矿产和能源部部长费尔南多向中国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舒印彪正式颁发了巴西美丽山水电送出特高压直流输电二期项目开工许可证。这是巴西基础设施领域的重点工程,其一期、二期均由国家电网公司中标并投资、建设和运营,建成后,将把巴西北部丰富的清洁能源电力远距离大容量输送到东南部的负荷中心,更好地促进巴西经济社会发展。
美丽山位于亚马逊河的腹地,那里生活着众多以捕鱼为生的原始印第安部落,环境和文化因素十分复杂。但国家电网公司凭借负责任的环保手段、大量的就业岗位以及令人惊叹的施工效率,赢得了地方社会的认可。
和巴西印第安人不同,中国民众对电,可以说是司空见惯到了熟视无睹的程度。用电的地方越来越多:炒菜做饭从燃气变成了电炉,取暖从烧煤变成了烧电,出行从燃油车变成了电动车。

但在很多人的认识里,电,以及电气时代,依然是西方文明的象征。电从哪里来,很多人也并不十分清楚,对于发电的印象,还停留在冒着浓烟的火电厂;输电,也无非是架杆接线。
但是,在输电领域,我国正创造着世界上最为领先的技术。中科院院士卢强曾说,在我国,真正具备自主研制和创新水平,并且能称得上伟大的工程,有,但不多。而特高压,则是名副其实的、伟大的自主创新工程。
伟大创新的背后,往往是曲折的、甚至反复的讨论和论证。早期,对于发展特高压的疑问主要集中在经济性与成熟度上。但截至目前,我国在特高压领域取得的成就,不但提振着我们的信心,也不断刷新着我们对于时代的认知。
以特高压交流输电为例,我国目前已攻克了完全稳定控制等多项技术难关,成功解决了特高压电网建设的安全性、稳定性、潮流分布及电磁暂态等问题,是第一个成功设计和运行1000千伏电压等级特高压交流输电工程的国家。
从时代背景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能源结构显著优化,到2016年底,非化石能源利用量占到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13.3%,水电、风电和光伏发电均领跑全球。将这些分布分散、且多地处偏远的清洁能源电力输送到东部能耗中心,正是特高压电网承担的重要任务。
除了新旧能源的互联,特高压还承担着全球能源的互联,将跨时区、跨季节的各大洲电网连接互通,实现世界范围内清洁能源的调度和利用。全球化、能源结构转型、基于智能化的万物互联,是我国特高压技术诞生的背景,也是其服务的时代,用应运而生、顺势而动来概括,再恰当不过了。
“平反”可燃冰
相对电的无处不在,可燃冰更像一个传说。
2013年,日本首次宣布从海底可燃冰层试验开采提取甲烷气体,成为这个能源进口大国的重磅利好。“可燃冰会让日本成为新能源大国”、“中国可燃冰研究已落后日本十余年”等说法陆续出现,让人们在为新能源振奋的同时,又不免感到一丝失落。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日本的试开采并不成功,因为遭遇到了泥沙堵住钻井通道的问题,所以被迫中止。
时间到了2017年。5月10日,中国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工程首次试气点火,并于7月9日试采结束并关井,持续试采60天,累计产气超过30万立方米,创造了产气时长和总量的世界纪录。试采使用的海上钻井平台“蓝鲸一号”,由山东烟台企业中集来福士自主设计建造,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双井架半潜式钻井平台。
但人们并没有忘记日本遭遇的挫折。可燃冰真的可行吗?与此同时,对可燃冰开采所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恐慌。“开采可燃冰将引发海床崩塌、海洋酸化”,“大规模商业化使用是天方夜谭”,“可燃冰不过是概念炒作”。
质疑源于不信任,也源于不了解。比如,很多人并不理解对于可燃冰的开采而言,“连续”二字意味着什么。
要做到稳定生产、从而实现可燃冰的商用价值,就需要对深埋于海床之下的固态可燃冰做到水、泥沙和甲烷气体的分离,这一点,正是可燃冰开采的世界性难题。
而我国在传统的加热法和降压法之间走出了一条新路,从单纯考虑降压,变为关注流体的抽取,在降低海底原本稳定的压力、降低可燃冰储层的成藏条件之后,再将分散在类似海绵空隙中的可燃冰聚集,最终达到水、泥和气的分离,实现了防沙、储层改造、钻完井、勘察与测试等方面的多项突破。
但证明“技术上可行”,仅仅是第一步。要不要用?怎样用?如何控制节奏?是手握新技术竭泽而渔式地开发,还是因为担心风险、担心被污名化而小心翼翼、亦步亦趋?可燃冰与特高压一样,也面临着一些伦理式的追问。
正是在追问中,方显理性、科学与公义。在可燃冰的试采中,我国一直对环境问题保持高度关注,在试开采的前六年间,先后在神狐水合物区组织了10个航次的野外调查,系统勘察了这一海域的地质、海洋生物、海底环境、海表大气甲烷等特征,对海底滑坡等地质灾害进行了系统监测,保证了整个开采过程的安全、可控和环保。
未来,可燃冰如果能实现大规模开发利用,将对我国煤炭依赖性能源结构带来重大改善。从社会大众的角度看,价格可控的、可广泛使用的替代性能源的出现,正是“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保障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
“正名”新核电
2015年12月,由中国商务部和南非贸易与工业部共同主办的中非装备制造业展在约翰内斯堡开展。在华龙一号3D模型前,习近平主席向南非总统祖马介绍说,“这是我们自己的技术,我们要把它推向非洲和全世界”。
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第三代核能发电技术。“完整自主知识产权”几个字意味深长。上世纪80年代,在法国和英国的帮助下,中国建设了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商业核电站——大亚湾核电站,当时,从水泥到电话线都需要从国外进口,国产化率仅为1%。而华龙一号的装备国产化率达到85%以上,六万多台套设备的生产、配套和组装,涉及上海、四川等28个省市、5300多家企业。
但相对技术上的高歌猛进,全球核电面临的是一个饱受争议、并且相对低潮的环境。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各国普遍放缓了核电建设速度。2015年《全球核工业状态报告》显示,全球核电厂开工数由2010年的15座跌至2014年的3座,全球核电占总发电量的比例连续3年低于11%。
在国内,对核电的质疑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几年来,题名为《十问内陆核电》《多余的核电》《反核电宣言》的文章屡见报端,部分社会公众的恐核情绪也再次滋长。
但对于核电的安全性问题,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设计施工者,都从来没有过丝毫松懈。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海牙国际核安全峰会上首次阐述了中国的核安全观:“荷兰哲人伊拉斯谟说过,预防胜于治疗。近几年,国际上发生的重大核事故为各国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历史悲剧重演。”2016年,国新办发布的《中国的核应急》白皮书也提到,“核事故影响无国界,核应急管理无小事”。
唤起人类恐惧的是新技术,平息人类恐惧的,则往往是更新的技术,这一点,华龙一号是绝佳的例子。不同于以往的核电技术,华龙一号根据地球重力和自然循环的方式,设计了一套能动与非能动相结合的安全系统,在无外部电源的情况下,依然能为核电站提供防护措施。它还采用了双层安全壳结构,不但可以抗9级地震、防大型海啸,还可以抵御商用大飞机的恶意撞击。
从核电本身来看,作为一个相对成熟的技术,它仍然是短期内替代化石能源发电的重要选择。中国工程院院士樊明武曾指出,要利用化石燃料所给的喘息时间,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水利、太阳能、燃料电池、地热等,而“要保证70亿到100亿人口在地球上活着并生活得比较好,原子能还是最可能的解决方案之一。”
而发电能力正是华龙一号最令人叹服的地方:若按照最大功率运行,一台核电机组每小时可以发电115万度,相当于100个普通家庭一年半的用电量,年发电量能满足一个中型城市一年的用电需求。从环保效益看,能减少标准煤消耗53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1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约21万吨。
正如不存在绝对的安全,对新技术的争议也不会完全消失,并需要系统的社会解决方案对其应用加以优化。但新核电的发展历程,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关心公众反应、容纳争议、也允许焦虑的包容精神。
美国社会哲学家芒福德在《技术与文明》一书中曾说,技术的有机平衡问题,为三大社会要素提供了最终出路:社会智力、社会能量和社会善意。“善意”二字,尤其引人深思。
当下,我国在能源领域多项世界级的突破,背后正是一个对新技术充满善意的制度和社会。
反过来说同样成立:善待新技术,就是善待我们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