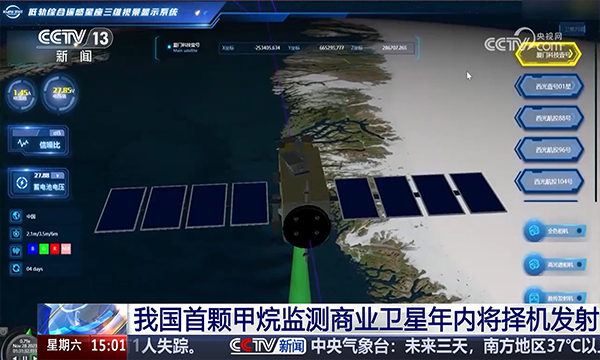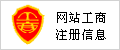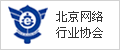自1978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煤电行业逐步得到全面、快速发展。主要体现在电力主体设备全面更新上、结构优化上、管理水平提升上;从指标看,体现在效率、可靠性、污染排放强度及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耗水强度、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发电成本等全面改进上。中国燃煤发电系统已脱胎换骨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先进的燃煤发电系统。
近十多年来,随着全球以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等低碳发展为特征的能源转型和以“大云物移智”为特征的技术革命急速而至,对中国以传统先进性为特征的煤电系统和电力系统带来巨大冲击。一方面我国顺势而为,奔上了能源转型之路,新能源发展风起云涌,但风电、光伏电能消纳问题及补贴问题严重。另一方面,由于电力系统适应新能源发展的系统调节能力不足,灵活性电源严重缺乏,使煤电成了调峰主力;同时,受各种因素的影响,煤电利用率和负荷率下降、煤电企业亏损严重。煤电行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改革开放四十年煤电脱胎换骨
1 电力总量大幅度增加,电力结构由水、火二元向多元方向转变
1978~2017年,我国电力装机容量及发电量分别从5712万千瓦、2566亿千瓦时提高至17.77亿千瓦、6.42万亿千瓦时,分别提高了30倍、24倍,解决了长期以来的电力短缺问题。
1978~2010年,我国火电发电装机和发电量长期占比分别在68%~76%、75%~83%之间波动(我国公布的统计资料是火电而未分煤电,据分析,煤电占火电的比重约为90%~95%,因此一般将火电数据近似为煤电数据),其余几乎全为水电。在改革开放初期,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基本为零。核电发电装机和发电量到2017年达到3582万千瓦、2481亿千瓦时。从“十一五”开始,风电、太阳能发电超高速发展,2005~2017年的十二年间,并网风电和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从105.6万千瓦提高至29267万千瓦(并网风电16325万千瓦、并网太阳能12942万千瓦),提高了276倍;发电量由16.4亿千瓦时提高到4200亿千瓦时(并网风电3034亿千瓦时、并网太阳能1166亿千瓦时),提高了255倍。197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即水电发电量比重为17.4%,到2017年水电、核电、并网风电和太阳能发电等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为30.3%。火电发电装机与发电量也分别由1978年的约69.7%、82.6%,到2010年73.4%、80.8%,下降到2017年的61.2%(煤电55.2%)、71%(煤电64.7%);在火电机组中供热机组的比重不断提高,由2005年的14.2%提高至2016年的37.0%,由此可见煤电仍占主导地位。
2 燃煤发电设备更新换代,能效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我国煤电超超临界机组在单机容量、蒸汽参数、机组效率、供电煤耗等方面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空冷机组、示范电站60万千瓦超临界循环流化床机组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在役机组广泛通过汽轮机通流改造、烟气余热深度利用改造、优化辅机改造、机组运行方式优化等,使机组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只有少数20万千瓦机组,而目前已形成以30万千瓦、60万千瓦、100万千瓦的大型国产发电机组为主力机组的发电系统。单机30万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比例由1995年的27.8%增长至2017年的80%以上,60万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容量所占比重达到44.7%。2006年年底,我国首台100万千瓦级煤电机组才投运,到2017年达到了103台。
2017年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火电机组供电煤耗309克/千瓦时,比1978年的471克/千瓦时下降了162克/千瓦时。单位发电量耗水量由2000年的4.1千克/千瓦时降至2017年的1.25千克/千瓦时,降幅近70%。与世界主要煤电国家相比,在不考虑负荷因素影响下,我国煤电效率与日本基本持平,总体上优于德国、美国。
3 煤电污染控制技术及设备不断升级,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领域不断拓宽
大气污染物治理方面:在烟尘(颗粒物)治理上,改革开放初期,电厂锅炉烟气平均除尘器效率约85%,上世纪90年代中期约95%,2000年达到约98%,2010年达到约99.2%,目前达到99.95%左右。在二氧化硫排放控制上,上世纪90年代由个别煤电机组建设同步引进国外烟气脱硫设备及技术,到2005年左右广泛引进脱硫技术开始大规模建设烟气脱硫装置,目前脱硫装置已全面覆盖煤电机组,平均脱硫综合效率已达98%左右。在氮氧化物排放控制上,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进低氮燃烧技术,并在90年代初新建30万千瓦及以上煤电机组全面采用;2003年前后通过新建项目从国外引进了烟气脱硝技术,“十一五”以大量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国产化烟气脱硝技术设备为主导辅之以自主创新,加快了烟尘脱硝工程应用进程;“十二五”开始大规模建造烟气脱硝装置,目前,烟气脱硝已全覆盖常规燃煤机组。
废水治理方面: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解决历史上一些燃煤电厂没有建设灰场、灰渣经水力除灰后排放到江河湖海的问题,如1979年有1028万吨渣排到江河,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到1995年底原电力部直属电厂全部停止向江河排灰。同时,燃煤电厂逐步普遍采用废水回收利用、梯级利用、改造水力输灰为气力输灰、提高循环水浓缩倍率等方式减少排水量。我国在火电厂用水优化设计、循环水高浓缩倍率水处理技术、超滤反渗透的应用边界拓展、高盐浓缩性废水处理等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
固废综合利用方面:燃煤电厂固体废物主要为粉煤灰与脱硫石膏。我国粉煤灰已广泛应用于水泥、加气混凝土、陶粒、砂浆等生产建筑材料,路面基层、水泥混凝土路面等生产筑路材料,回填矿坑、农业利用,以及提取漂珠等高附价值利用方面。“十一五”以来,随着电煤消费量的提高和脱硫装置的普遍应用,脱硫石膏产量不断增加,综合利用途径也不断拓宽,现已广泛应用于水泥缓凝剂、石膏建材、改良土壤、回填路基材料等。2017年,全国燃煤电厂产生粉煤灰约5.1亿吨,综合利用率约72%;产生脱硫石膏约7550万吨,综合利用率约75%。
4 煤电单位发电量污染物排放强度持续降低,污染物排放总量得到强力控制
通过结构电力调整、提高机组技术水平、实施节能减排建(改)造工程、提高运行优化管理水平等综合措施,中国煤电污染物排放强度不断下降、总量得到强力控制,已不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
从大气污染物控制来看,2017年与1978年相比,单位发电量煤电烟尘(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别为由约26、10、3.6克/千瓦时(1978年数据由作者估算得出),下降到0.06、0.26和0.25克/千瓦时。煤电烟尘排放量由1978年约600万吨,降至2017年的26万吨左右,下降了近96%;二氧化硫排放量由2006年峰值1350万吨,降至2017年的120万吨左右,比峰值下降了91%;氮氧化物排放量由2011年峰值1000万吨左右,降至2017年的114万吨左右,比峰值下降了近89%。
低碳电力发展方面,通过电力结构调整、技术进步、管理优化等措施,电力碳排放强度明显下降。据笔者估算,1978年生产1千瓦时电能,火电碳排放强度与全电力碳排放强度分别约为1312克/千瓦时(以二氧化碳计)和1083克/千瓦时,2017年降低到843克/千瓦时和598克/千瓦时,分别降低了35.7%、44.8%。
废水控制方面,2000年火电行业废水排放量为15.3亿吨,2005年达到顶峰约20.2亿吨,2017年降至2.7亿吨,较峰值下降了86.6%。火电行业单位发电量废水排放量由2000年的1.38千克/千瓦时降至2017年的0.06千克/千瓦时,降低95.7%。
5 电力工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政府强制性手段与激励机制相结合,共同推动了中国煤电脱胎换骨
保障电力充足供给及安全、高效、清洁发展,是电力工业发展的内在需求。正是改革开放,开拓了利用外资、内资办电的渠道;扩大了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的空间,通过对技术、设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加快实现技术及装备国产化;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学习国际先进管理经验,极大促进了电厂科学管理水平的提高。从政策和体制上看,在国家强制性节能、环保政策为主导,辅之以激励、引导政策的双重作用下,在电力行业国企占绝对优势地位、中央发电企业约占半壁江山的情况下,电力企业严格、快速贯彻节能环保要求,加快了中国燃煤电厂污染控制和清洁生产进程。
在改革开放初期,燃煤电厂污染排放约束主要是1973年年底由国家计委、基建委、卫生部联合颁布的《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中对“电站”烟囱排放的二氧化硫和烟尘的要求。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老帐逐步还清,不再欠新账”的环保指导思想下,煤电机组通过“以大代小”“以新代老”等方式,消减污染物排放,以及实现行业主管部门污染防治计划目标。在2000年以后,随着政府机构改革、环保管理强化以及电力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环保要求更多地体现在国家新环保目标、新环保部门、新行业管理部门的新政策体系上。如五年规划纲要体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大气、水、土壤治理等“行动计划”(简称“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以及各级政府部门节能减排“文件”要求,此外还有国资委、中央企业的自我加压等。其中,强制性、半强制性手段包括:项目准入、淘汰落后产能要求、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排放标准、能耗水耗限额控制、环境影响评价、节能评估、清洁生产审核等。激励性、半激励性手段有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价格等政策。在二氧化碳排放控制方面,除了节能要求不断强化外,近年来对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控制还提出了针对性要求,如国家颁布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大型发电集团每千瓦时供电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550克以内”、以及《电力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到2020年燃煤机组每千瓦时供电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下降到865克”。在水效政策方面,主要有取水许可、水资源费征收、计划用水管理和水资源开发利用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控制等。
在政策支持上,如通过提高环保电价,使环保成本传递到电力用户是最重要、最有效、最根本的措施。目前,燃煤电厂脱硫、脱硝、除尘设施建设及达到要求的电厂,上网电价每千瓦时平均提高了约0.027元人民币,现役机组超低排放电价每千瓦时一般再提高0.01元。
二、履霜坚冰,煤电要承担起支撑能源转型的新历史使命
1 煤电当前及面向未来的问题与挑战
一是煤电运矛盾、煤电与新能源和电网矛盾尖锐而具有长期性。煤电与煤炭是天生唇齿相依的行业,但我国的电煤供应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的电煤供应的长期性、稳定性相比有巨大反差。我国电煤供应在数量、价格、质量、运输上,长期以来未形成稳定、良性竞争关系,煤电矛盾起伏、尖锐,造成煤企、电企交替困难或双方困难,煤电运矛盾是能源发展中最复杂、难解的矛盾之一。近年来,煤价总体在高位运行,但“煤电价格联动”未能及时启动,成为煤电企业亏损的重要原因。煤电矛盾虽然反映在煤企、电企及运输企业身上,但根子却扎在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的矛盾上,扎在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上。煤电与新能源发展以及电网的矛盾是也电力工业发展的基本矛盾之一,具有客观性、系统性、长期性。体现在建设、生产和经营活动中,是新能源替代煤电所带来的传统电力系统运行规律变化和利益关系调整中的矛盾,是共同电力用户下,发电企业间在发展速度、布局、辅助服务责任、效益分配上的矛盾,总之,其核心是利益矛盾,不是能源道德问题。
二是煤电经济、环境、社会效益有效发挥不足。我国煤电机组虽正值年青体壮之时,但设备利用率、负荷率不足,存在有力使不出、大马拉小车的情况,经济效益、社会效率都受到严重影响。在回归电力商品属性的电力体制改革中,由于初期市场机制设计不完善,在大用户直购电、市场电量的争夺中,明显低于发电成本的恶性竞争方式,使已经大面积亏损的煤电企业不断饮鸩止渴,进一步扩大亏损面和亏损深度。
三是煤电节能减排的压力不减。电力工业每年转化了20亿吨左右的煤炭,如此大的用量必然是各级政府污染排放监管的重点。尽管对企业环保要求持续趋严,短短十年污染治理设施几乎处于不停顿的改造之中,能效、水效水平、综合利用水平、常规污染物排放强度已是世界先进甚至领先水平,但是对煤电继续强化清洁生产和监管要求的趋势不会改变,企业环保社会责任的压力、运行维护的工作压力将持续存在。
四是煤电高碳电力的帽子难摘。煤电是高碳电力的特性与生俱来,虽然单位发电量碳排放强度持续下降,但减排空间越来越小,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会随着煤电总量的增长继续增长一段时间。由于煤电机组平均年龄小,碳锁定效应明显,会成为中国能源电力转型的关键问题。对企业长期发展而言,二氧化碳高排放的煤电就是煤电生产和发展的“死穴”,而成本不断降低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就是打击“死穴”的拳头。即使煤电常规污染物排放再低甚至趋近为零——对环境质量改变已无实质性意义,但也遮不住高碳排放的本色;而今天越新、越大的燃煤电厂,在明天会因其高碳性反而会逐步变为发展的“包袱”。
因此,年青、先进、庞大的中国燃煤发电系统,在能源转型道路上既要承担支撑能源转型的新历史使命,又要经历“履霜坚冰”的艰辛,只有精准定位,扬长避短,才能功德圆满。
2 煤电在新历史使命中的任务及要求
一是煤电在近中期要继续发挥好电力、电量的主体作用。持续降低煤炭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大幅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使清洁能源基本满足未来新增能源需求,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量不断下降,是我国能源转型的战略取向之一。随着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煤电的主体地位最终将被取代,但当前乃至二三十年内煤电仍是提供电力、电量的主体。
二是因地制宜、适当开展提高煤电机组灵活性调节性能的改造。不论从当前解决矛盾的需要看,还是从发展趋势看,煤电机组要提高灵活性运行性能,使煤电机组能够更为灵活应对电力调峰问题,促进其他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煤电也将逐步转变为提供可靠容量与电量的灵活性调节型电源。但是要充分注意的是,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并不是煤电自身的需要,而是从能源系统、电力系统整体最优的角度考虑的一种不得已方案,是为补救不合理的电源结构以及电源、电网不配套、运行难协调的一种措施,而不应当成为一种常态。因此,改造方案应有其严格的条件限制,要有前瞻性眼光和系统性考虑,具体方案必须因地制宜,充分论证,技术措施与政策措施相配套,防止“一刀切”。
三是燃煤发电技术继续在清洁、低碳、高效、安全的基础上向适应性方面发展。一方面,煤电继续以高效超超临界技术和更低的污染排放技术为主攻方向,以二次再热超超临界燃煤技术、超超临界机组的高低位错落布置技术、650摄氏度蒸汽参数甚至更高温度参数的机组技术、以污染物联合、系统治理技术为主要研发示范重点;另一方面,根据煤电作用定位发生变化以及“走出去”需求,应从能源电力系统优化上、区域和产业循环经济需求上、用户个性化需要上,在新建或改造煤电机组时,有针对性地选择或定制机组形式(多联产还是发电)、规模、参数和设备运行年限。不能片面、极端追求高参数、大容量和高效率、低排放的普遍性目标,更不能“一刀切”禁止煤电发展。
四是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措施要向精准、协同的方向拓展。预计到2020年,煤电排放到大气中的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项污染物年排放总量会进一步降至200万吨以下,而且以后不会再升高。煤电对雾霾的平均影响份额可以达到国际先进的环境质量标准10%以内。随着排放标准制及环保要求提高,要真正落实以环境质量需求为导向(而不是以严为导向)的措施。要高度重视机组调节性能变化对污染控制措施的影响、污染控制设备稳定性可靠性经济性和低碳要求之间的协调、一次污染物与二次污染物控制协调、高架点源污染控制与无组源污染源控制协调、固体废物持续大比例和高附加值利用等问题。
五是煤电要发挥好调整煤炭消费结构作用,促进全社会煤炭污染问题解决。全球电煤占煤炭消费的比重平均约56%,美国、澳大利亚在90%以上,德国、加拿大、英国等在70%~80%之间,而我国约占50%左右,要持续提高电煤比重。同时要注意,提高电煤比重并不意味着提高煤炭在能源中的比重。
六是要让煤电有合理的、承担历史使命的经营环境,高度防范煤电生产经营困境演变为系统性风险。一个长期、全面、深度亏损的煤电行业,一个被过早唱衰的支柱性行业,一个靠改造设备性能、拼设备寿命、饮鸩止渴维持生产和员工稳定的行业,不仅支撑不了能源电力加快转型,而且会成为电力、能源、经济运行中的严重风险。
结语
煤电新历史使命是国情使然、规律使然。能源转型是历史必然,中国煤电支撑能源转型也是历史必然,但转型的道路是长期的、艰巨的、曲折的。如果我国不是一个将能源安全要求建立在14亿人口基础上的大国而只是一个人口小国,如果我国的能源资源不是以煤炭为主且煤炭产业与其他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我国煤电系统同美国、英国一样是由平均运行了四十年左右燃煤电厂所构成(现在还有55岁的燃煤电厂在运行)而不是现在只是十年左右的燃煤电厂所构成,如果我们没有在煤炭、煤电产业中沉淀大量的资本,如果我们的电力系统不是建立在以煤电为主体的基础上且电网承担着“西电东送”等大范围资源优化配置的任务,如果……如果我们不是在一张刚完成的、绚丽多彩的能源新图画上再添色彩,而是在一张白纸上画画或者是弃旧图新,那么我们就可以自豪地、高调地向全世界宣布,我国煤电正在寿终正寝。中国能源转型之难就难在我们不能把能源转型简单地理解为用一种能源勇往直前地去替代另一种能源,而是价值导向、因地制宜、多源协同、系统优化。能源电力转型成功如春蚕破壳,煤电犹如蚕茧之壳,不能时机未到茧壳先破!
原文首发于《能源情报研究》2018年8月
作者系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