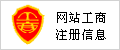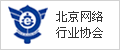20世纪三四十年代,澳大利亚东南部的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州出现了罕见的干旱,兔害横行,森林火灾不断,土壤风蚀也很严重。
受澳大利亚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委托,英国生物学家弗兰西斯˙雷克利夫率先对澳大利亚的土壤侵蚀问题进行了调查。
随后在政府官员的努力推动下,新南威尔士依据1938年的《水土保持法》建立了全澳第一个水土保持局。
1937—1945年,澳大利亚东南部各州都遭遇了严重的干旱。
1937年,新南威尔士州中西部的降雨“创历史最低纪录”;1938年,干旱加剧,并蔓延到澳大利亚东南部; 1944—1945年,在南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北部和新南威尔士州南部,强沙尘暴天气持续多日。直到1945年,澳大利亚南部的旱情才最终得到缓解。
除了干旱,澳大利亚的农田牧场还经受了二战所带来的社会和经济冲击。
在1942年新加坡陷落之后,澳大利亚的贸易通道受阻,农业技术也不能及时引进,再加上征兵所导致的农业劳动力减少,澳大利亚的农村社区面临巨大的环境和社会压力。
如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这段历史,我想探讨的是:对于那些关心土壤保护的人们来说,现在是不是应该研究一下关于土壤保护的叙事方式?
1930年代,美国大平原成为尘暴重灾区之后,澳大利亚的媒体对美国严重的水土侵蚀进行了广泛的报道。
在此期间,包括山姆˙克莱顿在内的澳大利亚的土地资源保护主义者,从美国关于土壤保护的有关报道中获得了很多启发。
就像1930年代的美国人那样,澳大利亚人在1940年代也非常担心土壤风蚀。
在关于沙尘暴的那些报道中,对永久性的生态退化的警告动人心魄。沙尘暴将会伴随着国家和文明的衰亡,要经过数百年才能恢复土壤的再生能力。这些故事跨越了国界,通过对沙尘暴重灾区的描绘,将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起来。
包括克莱顿在内的澳大利亚人,希望本国的宣传报道能促使澳大利亚民众正视土壤侵蚀危机。
克莱顿在1938年的《土壤保护法》中的那种叙述方式被大众媒体所效仿。民众的担心、战争和国家神话渗透到那些关于生态悲剧的报道之中。
1940年代报纸对土壤侵蚀的有关报道中,对牧场主提出了批评:由于超载过牧,牲口啃光了起保护作用的植被;小麦农场主也难辞其咎:他们开垦了过多的土地,使裸露的土地任由狂风侵蚀。
媒体报道中的那些图片显示,数以百万的家畜,甚至被视为害兽的兔子,在酷暑中痛苦挣扎,直至死去;牧场围栏被埋在巨大的沙丘之下。
澳大利亚会成为另一个“撒哈拉”吗?在新闻报道中,沙丘吞没了农场,男人们拿着铲子,奋力清除灌渠和铁路线上淤积的尘沙。
家庭主妇们整天都在尘土中忙活,而在沙尘暴中走失的孩子,更在报道中占据显著位置。
所有这些令人震惊的报道,是否放大了人们的厄运、愤怒和疑惑呢?
出现在这些报道中的图片和文字都值得我们好好探讨。媒体上的那些图片,让我们能真切地感受到水土流失及其影响。
我现在虽然致力于研究澳大利亚对土壤侵蚀的有关报告,但是我并不准备教导人们该怎样对待土地。
但土壤及其像地球一样久远的历史,却可以从多方面促进人类的思考:文明的兴衰,民众的恐惧和梦想,他们的神话和信仰,对与“自然搏斗”的感受,以及通过写作和摄影、电影、绘画等视觉艺术等形式,对所有这些内容的充满想象力的表达。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对环境思想史有更多的了解。
土壤漫长的生命,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当前,澳大利亚国内关于煤炭和天然气勘探的争论愈演愈烈,在这种形势下,我想对澳大利亚和中国的城市市民、股东、政府官员和学校的学生们讲出如下事实:
我们每一个人的食物都来自于土地。土壤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所有物种所能获得的食物的质量。不论这些物种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它们都取之于土地。不论是在沿海还是内陆,不论是在农场还是牧场,那些有经验的农民和牧民为生产食物,不得不抗击恶劣的气候和天气,控制害虫和疾病,同时还要应付各种不利的政治和经济局势,战胜孤独和抑郁。
农场主能切身感受到,土壤是脆弱的而非“可再生”的。他们也知道,土地保护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人们——不仅是农场主,还包括市民、股东和政府官员——对土地的珍惜。
综观土地的历史,从古至今,就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宣传资源保护的那些人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土壤,自然的平衡非常脆弱”。
我们需要善待土地,善待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