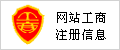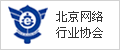政治意志力的实践是环保问题解决的第一要件。

台湾环保署具有一票否决权,至今还没有哪个公司敢环评不通过而硬开工的。
治理环境最重要的外因是人民的觉醒和支持,台湾成功最主要原因是环保教育。
环保很重要的观念是透明化,民众需要知道全部的事情,无论好坏。
我比较同情政府,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不要轻易承诺,应该开诚布公。
台湾的垃圾处理是公认的成功经验,堪称奇迹。人均每天垃圾清运量从1980年代末的1.143kg减至2011年的0.427kg,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这是台湾首任“环保署”署长简又新最为得意的成绩单,1987年,在台湾“环保烽火年代”,他受命组建台湾“环保署”,环保队伍从无到有。“那会在台湾爬山不用认路,因为跟着垃圾上去,跟着垃圾下来。”他回忆说。
之后,他历任台湾“交通部长”、“外交部长”,被称为“台湾最具影响力的新生代政治家”。如今,离开公职后,年逾六十,他重归环保事业,主持一家基金会致力推动企业应对气候变化和施行可持续发展。
他常说:“意识、知识、共识兴环保。”他觉得环保最重要的还是人,没有什么捷径。“改变人的思想行为是改善环境最快也最难的工作。”
他也格外关心大陆环境问题,从北京的PM2.5污染、黄浦江死猪事件再到山东地下排污,感叹这像极了台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他担心大陆走得太急,提醒道,“我相信明年北京的空气不会好,黄浦江也不会一天就很干净。我做环保署署长四年,前三年都非常艰难,最后一年才做通民众的工作。这需要漫长的时间。”他还说,“其实大陆环保立法很多都比我们细致,主要还是执行问题”。
2013年5月,记者记者专访了这位台湾首任“环保署”署长,细陈台湾在环保道路上的进退得失。
环评,台湾“环保署”有一票否决权
记者:在台湾,当“环保署”署长,有什么感受?
简又新:有很多感触。我体会到大自然是很脆弱的,反扑之力也大。这使得我的思考方向总会以环境整体为出发点。我当交通部长后,就曾让人换掉火车上的全部厕所,不把铁路变成“臭路”。当时,台湾火车上写着“火车进站时不要上厕所”,因为都是直接排放的。我也体会到环保工作的辛苦,都是发生问题才来处理。其实源头处理永远比末端处理来得容易。
记者:台湾当前的环境问题是什么?
简又新:更多是经济建设与环保之间的问题。首先是能源消耗,其次是核能第四电厂的存废问题。再次是重大经济建设项目的环评问题。最近台湾几个重大的经济建设项目都因环评没通过而被叫停。与大陆不同,台湾“环保署”有很大权力,环评非常严厉,因此也有不少人想:是不是有些过了?一旦环评不通过就叫停,将影响台湾未来的发展。
记者:你认为环评需要为经济发展做一些让步吗?
简又新:环评本身不涉及经济开发利益的考量。只是站在环境社会的角度上,一般国家的做法是有两本报告:环评和经济开发报告,并案送主管单位作最终开发与否的决定,但目前台湾“环保署”有否决权。
记者:如果台湾的建设项目叫而不停,会有怎么样的后果?
简又新:台湾“环保署”权力非常大,本身有一票否决权。台湾至今还没有哪个公司敢环评不通过而硬要开工的。万一动工了,社会及舆论媒体压力会很大,民意代表及公民团体的影响力也大,而且是有罚则,公司通常不敢违法开工。
记者:难道没有企业钻环评的空子,设法通过吗?
简又新:在早期时,可能会有公司避开环评。比如,一个项目开始是100公顷土地,已经做过了环评。后来变成120、130公顷,增加的部分就没有做环评。但现在都不会有了。环评过程最重要的是透明公开,并邀请相关利益人同时参加会议,作正反双方的沟通与辩论。不是闭门会议,民众都可以来旁听。
最重要外因是人民的觉醒
记者:台湾历史上也曾有过环境污染很差的时期,当时是什么情形?
简又新:那是在1980年代,我叫它“环保烽火年代”。当时工厂污染排放过多,人们求助无门,开始大举包围工厂,变成重大社会治安事件。都市垃圾增速也很快,甚至引发了乡镇“垃圾战争”——你丢到我这里,我丢到你那里。
1988年有一次,高雄市环保局局长对我说:“报告署长,我们有个好消息,昨天晚上我们终于可以看到星星了。”这是台湾环保历史上最坏的时代。“环保署”也就是在这种烽火年代中诞生的。
记者:环保队伍是如何从无到有的?
简又新:“环保署”成立后,从中央建立核心团队,并协助建立各县市环保局团队。我们很幸运在1988年录取了三百多位平均32岁、有热情、有使命感、高学历的年轻人。从政策、立法、教育、环保基础建设、稽查等建立制度、培养人才。这些人基本上都没离开,所以后来二十多年的政策可以延续,他们也成为现在台湾各地重要的环保官员。团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记者:那时的台湾环保工作会否也阻力重重?
简又新:会有。环保是得罪人的工作,又难有政绩。我们与“经济部”成立“联合工业减废小组”,从源头做污染管制工作。但地方首长就不一定支持。环保官员通常是处于政府组织内的弱势地位,若地方首长不支持,很难开展工作。
那时候,我非常了解一件事——环境问题难管。我1987年上任时,对环境的改善根本不敢有奢望,因为牵涉的面太大,污染源太多,没想过短期内会有结果。所以当时定下的目标是到2000年会改善。
记者:最终促使台湾环境改善的最重要的外因是什么?
简又新:是人民的觉醒和支持。因为我们一直努力,发现政府也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必须要汇集全面的环保洪流来工作。当时“环保署”花了非常多时间和力气来做环保教育。其次是社会舆论的压力,大众媒体扮演决定性的因素,兼具了批判、督促与社会教育的多元角色。
环保教育,决定成败
记者:环保教育具体是如何做的?
简又新:环保教育是台湾环保工作成功的最主要原因。我们运用媒体做宣传,把环保教育写进学校正规学程中去。
环保教育要从儿童做起,我们称为“小手拉大手”。因此,每项政府计划都会有很好玩的名字,“拿破仑计划”(回收废轮胎)、“鲁班计划”(工地污染防治)、“飞鹰计划”(直升机寻找空气污染源)等三十多个计划案。我们还有很多有趣的活动,比如“外星宝宝”垃圾桶。
其实,每一次环保危机都是全民教育的最好时机。危机之后,我们被大家骂得乱七八糟。但因为所有媒体都报道,正是最好的教育时机。我们会把危机化为契机,把很多事情都说出来。
记者:这样不等于自爆其短?
简又新:不怕自爆其短,只怕有错不能改,隐瞒污染常常会造成更大的困扰。在今天网络与通信如此便利之时,很难隐藏环境污染上的秘密。环保很重要的观念是透明化,只有透明化才会建立民众和企业互信。
记者:遇到危机,民众会不会质疑“环保署”的执行力和公信力?
简又新:如果“环保署”透明化处理,通常民众会站在“环保署”的立场上的。大部分民众其实是很好讲话的,只要肯认错、能改,大家还是会愿意接受和相信。公开道歉是常有的事,在台湾处理危机第一件事就是要道歉,企业也不敢多讲话,首先出来道歉,再赔偿。
记者:环境NGO扮演了什么角色?
简又新:NGO是因环保事件而产生的,和政府的关系是“既联合又斗争”。在台湾,NGO和政府在污染治理上是完全联合的。每当有环境问题出现,都会有很多人跳出来说话,也会帮政府出主意。但在处理完污染事件后,NGO也会监督政府,有时候也很厉害,甚至会在报纸上“开骂”,说进度太慢了!
不要轻易承诺,应该开诚布公
记者:你最近在关注大陆什么环境问题?
简又新:我非常关心北京及各大城市的空气污染、都市垃圾的高速成长与处理,以及河川污染和地下水超抽问题。其实这些在台湾都发生过。
大陆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非常快,是压缩式的高速成长。可惜的是,环境问题也是“压缩式成长”地爆发。这与台湾以前相似。不过,我对大陆的环境治理是比较乐观的,以大陆“压缩式成长”的行政执行力,会很快看到成绩。
记者:大陆环境形势严峻,你为什么会乐观?
简又新:首先,中央政府了解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如果环境问题不改,会牵涉到维稳问题,大陆很怕出现群体性事件。其次,年初的北京空气污染与上海黄浦江的万头死猪漂流事件,给了大家一个震撼教育。再次,政治意志力的实践是环保问题解决的第一要件。就国际水平而言,中国的行政执行力是属高阶,有利推动环保工作。而且政府也编列了巨额预算,所以我的看法是很乐观。
记者:PM2.5是大陆目前最焦点的问题,你觉得短期能治理见效吗?
简又新:环保问题不是一天造成的,也不可能一天或短时间可以解决,需要全民的了解与讨论。政府过于强调PM2.5可能给人民太高期望,如果以后无法达成,会造成人民的反弹。
其实我比较同情政府,不可能改变的事情不要轻易承诺,应该开诚布公。民众需要知道全部的事情,无论好坏。但也需要给民众讲清楚政府的计划,民众是可以理解的。
记者:你认为台湾可以供大陆借鉴的最重要经验是什么?
简又新:说穿了就三件事情,一是赶快把民众教育起来,人民同时也是环境的破坏者。当人民有自觉性和共识的时候,环保就很好做。台湾民众以前也觉得环保是政府的事,其实大家都有份。其次是政府要协助成立民间公民团体,从事环保公益工作。台湾NGO非常多,影响也蛮大。社会需要这些监督和压力的。还有一点是媒体和舆论非常重要,真的是很重要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