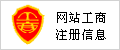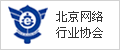从泰山脚下的泰安市,到沂蒙西麓的临沂市平邑县车行超过120公里,说起弘毅生态农场的苹果,司机祝志杰语调上扬,“你不知道,别的真的比不上”。
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蒋高明创办的弘毅生态农场2006年落地平邑县蒋家庄,因为北京来的师生、记者络绎不绝,一年后,祝志杰开通了一条平邑直通泰安的路线,这几年生意红火,老祝再添了两辆车,“我们带动了一个产业”,副驾上的蒋高明笑称。

前不久,蒋高明又发现了一株无心插成荫的柳。
9月2日,他在科学网的个人博客主页上贴出了发表在《环境教育》杂志的文章——《调查:千疮百孔的中国农村》(下称《调查》),互联网时代,文章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传播开来,弘毅生态农场的微信公号第一次出现了单篇文章近50万的阅读量,《半月谈》等知名媒体亦随之刊载。
调查所涉的蒋家庄只是蒋高明的家乡,他所描述的,也只是在当地的所见所闻,对于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而言,这甚至算不得一篇严丝合缝的“调查”。
蒋高明通过十年生态农业实践发现,易攻克的是技术,难破解的是社会。
环境问题屡见不鲜的今天,一篇调查何以受到这样的关注?也许是因为“千疮百孔”的,早已不止这一处家乡。

弘毅生态农场的有机果园。
家乡再调查
北方的9月天高云阔,鲁南大地无际的田野正在迈入秋收季节,波斯菊粉紫摇曳盛开了一路,车过处,嗅到的是暴晒过后的花生焦香,这似乎正是典型的、理想中的中国乡村模样。
显然蒋高明不这么认为。
马路的一半都摊着新拔出的花生,黑白两色塑料农膜俯拾皆是,半年的日晒风吹后,依然耐用的农膜是直接把花生扎成捆的好材料,事实上,家家户户也都是这样做的,“这些农膜肯定是要进牲口肚子里的,土里的就更多了”,蒋高明顿了顿,“但一直都是这样”。
蒋高明对家乡的观察并不是一时兴起,7月13日,《乡村调查之一:空气中充满令人窒息的臭味》一文首次在他的个人博客上发布,接下来的8天内,同一系列的十份乡村调查逐一面世,涉及水、空气、土壤、垃圾、农村殡葬等环境污染及社会问题。
8月,《环境教育》杂志联系到蒋高明,将十篇文章综合整理为《调查》一文:“自2005年以来……我们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很多变化。其中印象最深的是,这10年的生态农业实践中,中国农村的污染问题不但没有改观,反而越来越严重。由于普遍采取了违背自然规律的生产模式,同时城市垃圾大量进入农村,发达地区淘汰的产业在落后农村落地,因此,农村中出现了多种污染。本文章所反映的问题,是我们通过调查发现的真实现状。”
蒋高明2005年成为山东省首批“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次年7月,蒋带着“生态农业”研究课题和一支由十多个人组成的科研团队回到家乡,高价承包了约40亩低产田,办起了“弘毅生态农场”。
他的农场严格执行“六不用”原则:不用化肥、不用农药、不用农膜、不用添加剂、不用除草剂、不用转基因。

聪明人办傻事
今年天旱,村民蒋怀金菜地旁的水塘好不容易在雨后积起了水,趁着周末,他带上水泵下地,准备给干渴的大葱地浇一浇水。
蒋怀金的四亩地离弘毅生态农场的小院不过200米,站在马路上踮起脚,可以透过随风起伏的玉米尖儿,分辨出农场里的两层小楼和牛棚顶,这么多年来,带着博士生种地的蒋教授来来去去,但两个老同学几乎未曾谋面。
蒋怀金和蒋高明从小学起到高中都是同班同学,他还记得蒋教授在上学时,经常揣着包“知了猴”在教室吃。高考之后,两人的人生轨迹倏然岔开,落榜的蒋怀金开始打工务农,蒋高明在山东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毕业后,又于1988年和1993年在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开始了植物与生态系统方面的研究。
“他比较聪明”,蒋怀金笑道,而聪明人选择“六不用”的方式回乡种地,更让乡亲们不能理解:“这不明摆着是要绝产吗?”
蒋怀金种地沿袭的是农民多年摸索下来最经济简便的模式:化肥来肥土,除草剂可省人工,农药防病害,地膜则既保水又防杂草,他种地的目标也和其他农民殊无二致,提高产量才是普世标准。
“健康?我们都知道用(农药)这些不健康,但是没有办法,不用不行。”蒋怀金说。
站在去往农场的小路上可以看到,即便在离小院最近的耕地里,仍是大片翻卷的白色农膜。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一连询问了十来名正在自家地里拔花生的村民,他们均表示即便知道蒋教授的“六不用”理念,但种地仍离不开老三样,多数人对更“健康”的耕作方式也只是笑笑:“我们也没这个条件”、“上哪儿弄(有机)肥料”、“卖不出去啊”、“没人来除草”。
不用不行带来的是怎样的后果?蒋高明曾对媒体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单位耕地面积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化肥施用安全上线的1.93倍,但利用率仅为40%左右;农药平均施用量13.4千克/公顷,其中高毒农药占70%,有60%-70%残留在土壤中。
我国每年约50万吨农膜残留在土壤中,残留率高达40%,这些农膜在15-20厘米土壤层形成不易透水、透气很差的难耕作层,很难被分解。
在耕地资源被大量占用、农业人口不断流失的情况下,农民在极有限的耕地资源上追求最大产出,其结果必然是农业的化学化程度不断增加。
换句话说,农业活动对农民造成的直接健康损害只是开端,接下来的土壤污染、食品安全问题才是潜藏的巨大隐患。同样,要解开农业污染这个结,就应该溯流而上,从农业模式,甚至是社会结构上探索起。
蒋高明说,他推行的生态农业就是要争取破解这种恶性循环,从技术上打破化学依赖、从结构上改变农民脱离土地的现实,建立起良性的循环模式。
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
破旧立新的信心来自另一场生态修复实验。
2000年,为了遏制沙化趋势,国家紧急启动“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中科院西部办公室在新疆、内蒙古、西藏、陕西、四川启动了五个生态恢复试验区示范项目,其中在内蒙古启动了“浑善达克和京北农牧交错区退化生态系统恢复试验示范研究”重大课题,蒋高明成为浑善达克腹地正蓝旗试验区的负责人。
正蓝旗的巴音胡舒嘎查(村)有72户288口牧民, 土地12.6万亩,而全嘎查牲畜数量达11566头。要调整这片沙地的生态,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牲畜越冬的口粮问题,中科院的专家围封严重退化的4万亩土地进行试验,将其中1000亩种上只产玉米秸的英红玉米作为牛羊的饲料,用“以地养地”的模式,让其他退化土地上的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
连续10年的生态恢复实验有一个让人惊喜的开头。就在第二年,围封区内的草长到了半人高,这是连当地牧民都没有见过的景象,以前靠人工种植难以成活的小红柳,三年之后开始自然生长。
几年时间内,巴音胡舒4万亩严重退化的沙地草地恢复到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植被恢复了,野生动物也陆续回来,周围的嘎查纷纷仿效巴音胡舒的做法,一些曾严重退化的流动沙丘已经覆盖了良好的植被。
“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有了一个成功的先例,但耕作毕竟和放牧不一样,离了化肥农药,本就贫瘠的土壤上怎么产庄稼?
实际上,通过分析比对,蒋高明在此期间提出了新的农牧业模式:“畜南下,禽北上”。“畜南下”即利用农区大量废弃的秸秆养牛,接着牛粪还田,以有机农业逐步取代化学农业,提高农民收入,这是传统北方牧区不具备的物料优势,蒋高明信手拈来一串数字:“全国18亿亩农田除生产了约5亿吨粮食外,还生产了7亿多吨的秸秆,其中的95%以上可以通过技术转化成为牲畜的优质饲料”。弘毅生态农场正是由这一理念发展而来。
目前,农场喂养了近两百头肉牛,新建的蓝顶牛棚未来还可以将存栏量提高一倍。原本的“废物”,甚至是污染物,全都变成了生产链条的一环。

饲料加工的图片现场拍自弘毅生态农场。
农场的检测数据显示,2007年,20厘米内土壤层的有机质含量是0.71%,全氮的含量是0.058%;2014年,相应的数据增长到2.41%和0.247%。除了土壤营养元素和有机质升高外,土壤微生物和动物群落也开始恢复,多年不见的蚯蚓开始回到农田。
参与者
在承包之初,弘毅农场的作物产量的确赶不上周边农田,这片地原本是村里的晒谷场,产量低到连田都算不上,但从2008年开始,坚持“六不用”、只施有机肥的田地,开始显现出了“自然之力”的作用,各项作物的产量逐渐追平村民们的数字。
在今年大旱的情况下,弘毅农场的花生亩产达到了807斤,远高出周围用地膜、化肥、农药、除草剂方法的产量(400-600斤/亩)。
湖北宜昌三峡广播电视台的导演许扬是今年4月份了解到的弘毅生态农场,中国乡村发现网的文章标题直截了当——《蒋高明用8年实践宣告:搞生态农业不会饿死人!》,但许扬产生了疑虑:这样的模式,究竟能不能向农民复制?“如果可以的话,那就是农业革命”。
就这样,他辗转联系到蒋高明,并在6月9日来到蒋家庄,许扬打算做一个生态农业的纪录片,将弘毅生态农场的发展历程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
“我的想法是,生态农业技术的可复制性是问题关键。技术必须影响中国农民或农业主流技术。现在还处于为极少数人提供有机食品阶段,意义就小;如果可复制,未来大有希望。”
许扬打算十月再去蒋家庄,继续解答他预设的问题。虽然偏见可以用事实打破,但所有人都不敢妄言成功。
村民蒋庆礼在2014年与弘毅生态农场合作种植了20亩花生,弘毅出标准和技术,提供有机肥并负责后期收购,蒋庆礼则出人力来管护,“比如麦子的市价是1块多,我们收3块,总之我们就是把所有的风险都担了,他们就负责种。”即便如此,蒋庆礼还是弘毅“农场加农户”模式推广到的第一人,在蒋家庄,务农基本上只为了自家口粮,年轻人都走了,老人们即便想通过种地来发家致富,也难以承担过大的劳动强度。
9月13日这天在弘毅农场周边地头劳作的人中,只有一个80后的年轻人——和婆婆一起收花生。蒋家庄不过是千万个空心化的村庄中最平凡不过的一个。
社会、经济、生态
但蒋高明的信心仍是充足的,由于2013年弘毅生态农场的淘宝店上线,农场产品市场化的栓塞被打通,从生产到销售,“弘毅模式”也开始走上良性循环。
在网店首页,许扬制作的纪录片《心中一亩田》3分钟预告被放在产品之前。“50万是今年的销售预期,不过天旱,能不能完成这个目标还不好说。”农场科研助理、同时也是网店创办人的曾彦介绍,现在网店的顾客基本纯靠口碑和熟人积累,基本不做推广,这条唯一的视频算是最大的“广告”,即便如此,网店的销售规模也在稳步上升。
市场化也直接拉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今年新增的两户合作农户负责种植畅销的姜和小麦等作物,光是合作田,2015年的种植规模已超过了100亩。到12月,弘毅几年前成立的“乡土生态种植乡村合作社”,就会再次“复活”。
建立中国第一个“社区支持农业(CSA)”农场、以“洋插队”闻名的石嫣在2009年来过弘毅生态农场,她也认同蒋高明的“六不用”理念。
“一种农业模式的价值应从社会、经济、生态三个层面衡量。”石嫣说,“重点是(农业模式)有没有真正解决过去三农问题的痛点,农民有没有因此受益,农业有没有因此变得更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农村有没有因此成为更多人返乡的根。”
农业不会只有一种模式,不管是蒋高明还是石嫣都认同这样的观点。但蒋高明也总是笑言,如果弘毅模式推广开来,化肥厂、农药厂肯定要第一个玩完儿,这样下去触动的利益链条不可想象。
“弘毅模式主要是在农业生产方式上的创新,种养殖循环的模式,这样的一种生产技术如何能够让更多农户学到,可能不是弘毅模式本身的问题,蒋老师作为一个科学家身体力行做试验,而涉及到农业政策和农技推广那就需要政策上的改变了。”石嫣道。
而弘毅农场成立近10年来,已带动蒋家庄10户农民秸秆养牛160头,林下养鸡30000只,养蛋鸭300只,甚至带动了蒋家庄村容整治街道900米。
实际上,最开始蒋高明的这场试验确有课题经费的支持,近两年则基本是自给自足,而在困难时期,他曾把当选为“泰山学者”的50万元津贴投进了农场,从政府拿到的最大进项,是2014年平邑县畜牧局给的30万元养牛补贴。
“好像是这么多年的第一笔补贴啊”,蒋高明曾对媒体记者自嘲。“态度肯定是支持的。”村里的书记周京林回忆,“现在(政府)确实还没有什么实际行动。”

政府的行动
蒋高明每月回一次平邑,9月12日的这次动静不小,下午3点过,祝志杰的车载着蒋高明前脚刚到农场,后脚便来了村里和镇上的领导。《调查》一文发出后,当地父母官可能是第一批“忠实读者”。
蒋家庄隶属于卞桥镇,和全国所有谋求发展的城镇一样,这里因盛产石膏被冠以“石膏之乡”的别称,就着桌上的一杯金银花茶,卞桥镇党委书记高庆用家乡话和蒋高明聊起了近些年蒋家庄的发展。
“他们肯定会紧张”,蒋高明说,以往面目模糊的“中国农村”突然有了具体的指向,就像黑暗中突然出现了一盏聚光灯,不管这里照亮的是什么,总能吸引一些或惊或疑的目光。
平邑县2014年开始进行“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通村的硬化公路、沿途绚烂的波斯菊,都是在山东农村环境综合整治措施之外,平邑县的“更上一层楼”之举。
与书记一道过来的卞桥镇副镇长唐贞强分管农业,他对《调查》一文有自己看法:“如果是几年前的话,那这篇文章是符合的,现在就不是这样。”
文中第一部分提到的臭气熏天的养鸭场已在年初拆除;自2014年推行垃圾处理城乡一体化后,平邑县下辖农村的生活垃圾已经实施了市场化管理,按户籍人口每人每年收50元管理费,每家每户门口放一个240升的垃圾桶,每天由县里的环卫公司统一清运。
实际上,这还是唐贞强第一次听说“六不用”,他之前以为弘毅农场只是一个博士生的实验基地。“产业化是可以做,但要做五百亩一千亩,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来流转土地,流转就是钱,当年承包的价格到现在就远远不止了,这一个点就很难带起一个面来。还有后期的维护,水、有机肥、人力都是问题。”
他直言,现在老百姓看重的就是实惠,就是要挣钱。在农场工作了五年的曾彦也认为,弘毅模式要获得农民参与,只能把自己先做起来,变成“教科书”,让农民看到可行性,否则不论从什么层面来推广都是白搭,这也是农场至今只选择熟识的、认可度高的农民加盟的原因。
在卞桥镇,农业对经济的贡献与繁荣的矿业相比微乎其微,考虑到前期投入、人力成本和后期的科学管理,唐贞强坦言:“这种模式要推广到全镇,真的不好说。”但他支持弘毅农场在蒋家庄做一个点,“做成景点、旅游点”:“让投资者投三千万五千万也得让人看到什么时候能回本儿,如果这里是一个景点,带动了客流量,投资者的信心或许会大一些。”
实际上,弘毅农场一直受各路投资者青睐,然而蒋高明也一直保持单干状态:“资本投入以后,自主权就不在你手上了。”但生态旅游这一观点已在变成现实,到年底,农场最初的选址上将落成投资百万的有单间宿舍、会议室、厨房等完整设施的仿古建筑,专门招待前来学习、参观、考察的人。

乡村巨变
据镇领导介绍,虽然“美丽乡村”推行后垃圾管理已经卓有成效,但对于农膜、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物品,政府层面的管控尚处于空白状态。
可见的污染不见了,污染却并没有消失。
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何才文9月20日表示,我国耕地土壤长期处于亚健康状况,存在退化面积大、污染面积大、有机质含量低、土壤地力低等“两大两低”问题,目前我国耕地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比重达40%以上,具体表现为东北黑土地变薄、南方土壤酸化、北方土壤盐碱化;全国耕地重金属点位超标率达19%以上。
水土不分家。蒋家庄有926口人,村民们介绍,目前已有近70%的人家买山泉水来喝,“沿沂蒙山金线河两岸的十几个村庄,当年都是到河边沙滩取水喝,或者每个村里都有井,喝的就是浅层地下水。”蒋高明在《调查》中写道。
据澎湃新闻走访,现在蒋家庄的浅层地下已难打出水,金线河更指望不上,由于上游屡禁不绝的屠鸭场和养殖场,不下雨的时候,隔着百来米都能闻到臭味,而有的村民们之所以不愿喝镇上的自来水,主要原因是“碱太大了”。
蒋高明在《调查》中的第二部分就写到了水污染,金线河在20年前也有这样的模样:“夏天发洪水时可以在浅滩上抓到几十斤重的大鲤鱼,水流平缓时也能看到一些鱼儿在浅浅的水底下静静地呆着,孩子们用笊篱就能捞虾”。
而在20年后,卞桥镇制定的《平邑金线河省级湿地公园总体规划(2014-2020)》中,劣势一栏下这样写道:湿地南北狭长,地跨平邑卞桥镇南北,周边生活污水、面源污染、人为对湿地资源的开垦和蚕食等干扰较为严重。此外,保护和科研设施建设不足。
早在21世纪初,中国科学院章力建等专家已提出过农业环境立体污染概念:由农业系统内部引发和外部导入,包括生产过程中不合理农药和化肥的施用、畜禽粪便、农田废弃物处置、耕种措施以及工业污染等,造成农业系统中水体-土壤-生物-大气交叉污染。
公开数据显示,1997年至2007年的十年间,山东农药平均施用量最高,达157961.7吨,是最低的西藏地区施用量的206倍;作为全国的蔬菜种植基地,山东省十年来的农膜平均使用总量也是最高,有273127.9吨,是西藏的703倍。
在2015年的全国人大新闻中心记者会上,环保部部长陈吉宁介绍,到2014年年底,政府对农村污染治理已经累计投入255亿元,治理了约5.9万个村庄,受益人口达到1.1亿人。而到2015年,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
蒋高明离乡在外的这段时间,正是中国乡村发生巨变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