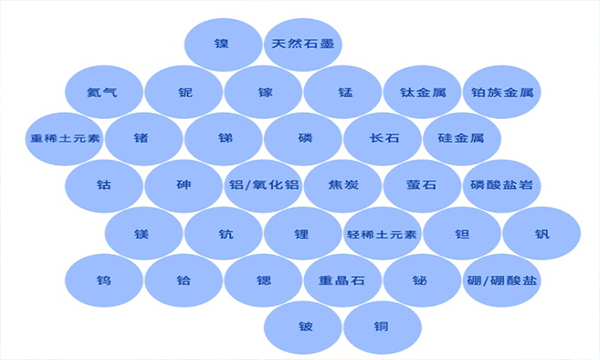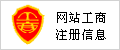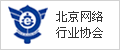一个世纪的法律建设、经济效益的“无形之手”和大刀阔斧的城市规划,伦敦最终为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空气治理经验。
1952年12月5日清晨,伦敦上空出现高压脊,近地气温发生反常降低,近地空气在低气压影响下形成冷气层,伦敦出现由地面向上,空气温度逐渐增加的逆温层现象,这使得伦敦城中的雾气不能逸散,不断增加。
伦敦上空烟雾弥漫,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粉尘在空气中久久不能散去。大量的有毒空气在伦敦城中聚合。伦敦居民取暖使用的烟煤含硫量更是高于工业用煤。粉尘中的三氧化铁、废气中的二氧化硫加上大雾中的水汽最终形成了硫酸。腐蚀性的硫酸附着在烟尘上或凝聚在小水滴中进入人的呼吸系统。

在烟雾事件前一周,伦敦城共有2000多人死亡,这一数字基本与一般年份持平。但是随后一周,就有超过4000人死亡。而伦敦城的死亡率在雾霾事件第八和第九天达到顶峰,每天有超过900人死亡。
英国官方就伦敦雾霾事件给出的报告认为共有4000多人因为雾霾事件丧生。但是高于正常年份的死亡率直到圣诞节时才出现回落。这段时间内又有8000多人丧生。准确人数并无定论,但是大多数人还是认为12000才是伦敦烟雾事件造成的实际丧生人数。
尽管政府认定死者只有老人和呼吸道疾病的患者,但是事实上,4000多名死者中只有三分之二是超过65岁的老人,45-64岁市民的死亡率是正常年份同期的三倍。此外,伦敦雾霾事件期间,婴儿的死亡率也是正常年份的两倍。
开始于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为大不列颠帝国带来了殖民地、原材料、世界霸权和无穷尽的财富。这一切都基于煤炭为蒸汽机提供的不竭动力。然而大量燃煤的背后则是日益加剧的空气污染。滚滚浓烟,成为了人们脑海中工业革命的象征。
伦敦城位于大不列颠岛东南侧的盆地之中,南北山岭环抱,泰晤士河自西向东奔流而过。温暖的大西洋水汽毫无阻碍的被吹进伦敦城,然后在盆地之中受冷凝结,形成漫天大雾,并且循环往复,久不消散。
伦敦城自罗马时代起就享有“雾都”美誉。而工业革命之后,这一美誉成为了对伦敦空气污染的最大讽刺。早在1813年就有了关于伦敦城烟雾缭绕的报道,而1873年,伦敦更是出现了首起有毒烟雾致人死亡的事件。
到20世纪初,伦敦已然变成了一座黑色的工业之都。由煤炭支撑的工业革命让伦敦城内遍布工厂,著名的伦敦东区位于伦敦东部港口附近,这里是传统工业区,服装、印刷、卷烟、制鞋、家具、食品等企业林立。整个伦敦城烟囱林立。
与工厂烟囱交相辉映的是传统守旧的英国人数百年不变的烧壁炉取暖习俗。伦敦城内无数的烟囱和壁炉消耗着无数烟煤,昼夜不停地向空中排放着大量烟雾。
烟尘与雾混合变成黄黑色,经常在城市上空笼罩,多天不散。伦敦环境污染严重。楼房上积满烟垢,泰晤士河生物绝迹,河水恶臭。当时,连紧靠泰晤士河的议会大厦,夏天也不得不关紧窗户。
伦敦糟糕的空气甚至为自己赢得了“伦敦雾”这一专有名词。伦敦雾气之浓,又被称为“浓汤”,在文学家的笔下,伦敦更是充满了肮脏油腻的空气,和在这空气掩盖之下的无数丑恶。
残酷的现实将伦敦城驱赶到了改变的十字路口。然而伦敦城乃至整个英国早就开始了一场针对空气污染的大博弈。
治理博弈
伦敦独特的环境曾意外催生出了世界首个有关空气污染防治的法令。1306年夏天,伦敦空气中弥漫的因烧煤而产生的刺鼻味道让前来伦敦参加国会的英国贵族们感到心烦意乱。这些地位尊贵的人发起了一场示威,反对燃煤。在这种形势下,国王爱德华颁布了禁煤令,规定初次用煤的人将被给予重金罚款,再犯,则毁掉熔炉。
这个看起来有些荒诞的故事在今天看来却有着无比强大的前瞻性。事实上,英国针对空气污染的治理确实并不算滞后。
1863年英国议会就通过了首部《工业发展环境法》(也称《碱业法》)。在那之后,《碱业法》经过了多次修订,同时英国议会也多次颁布其他空气污染防治的相关法律。
但是英国的空气污染治理涉及多个政府机构,包括地方政府、中央的环境部(主要涉及碱业检查团)等。而在公共卫生和环境事务方面,英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有着巨大分歧。地方当局一直是对个人和商业行为进行控制的倡导者,而中央政府则以保护个人自由为名阻止地方当局获得更多的管辖权。
中央机构和地方当局各管一面,一方权利的扩展意味着另一方权利的削弱,二者始终关心的是自己的权限,因而摩擦不断。
1952年伦敦烟雾事件和1956年《清洁空气法》为解决中央和地方的掣肘提供了契机。二者的分工以技术难度为标准:碱业检查团控制注册工厂的排放物;而地方当局则控制其他非注册领域的排放物。
新的划分标准却在商业企业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企业在自己的管理归属上与政府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大量的工业企业都希望自己的企业以注册工厂的方式纳入碱业检查团的管理中。
正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理念不同,才带来了企业这样一边倒的倾向性。因为企业有可能无法达到《清洁空气法》的要求,而纳入碱业检查团的管理,让他们有机会利用中央政府的态度,从而不完成法律要求,维护自己的利益。
尽管遭到了地方政府的强烈反对,但是在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1958年的碱业条令还是大大增加了注册工厂的数量。这不仅强化了碱业检查团的权利,也进一步加深了中央和地方在环境治理上的利益竞争。
与政府企业之间汹涌蓬勃的激烈交锋相比,身处社会底层的普通民众则表现出了出人意料的态度:他们既是空气污染最直接的受害者,同时也是环境治理的一大阻力。
以矿工为例,免费烟煤的大量分派一直是矿工薪金的一部分,一旦改用无烟煤,意味着矿工要多出一笔使用无烟煤的支出,因此矿工肯定不愿意使用无烟煤。
此外,改用无烟煤对于矿工来说不仅意味着与他们的收入直接挂钩,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改造燃烧设备的成本。新的供暖设备改造并不由政府提供所有费用,地方政府和户主还要分担约3成的成本。尽管政府有着改造补贴,但是补贴不足甚至没有发放补贴也使得户主和使用者缺乏改造设备的利益动机。
更重要的是,空气治理不仅关乎每一个人的生活,更是会深刻影响到煤炭工业的命运。因此煤炭工业发达地区的烟雾控制计划进展更加缓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环境问题也逐渐走出了各国孤立的传统概念。英国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但是空气污染物却漂洋过海,危害了欧共体其他国家。例如,英国就被证实是20世纪50、60年代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酸雨的主要污染源。
而在一百多年空气污染治理的过程中,英国一直没有具体的空气质量标准,这无疑与欧共体环境治理理念存在差异和冲突。这种差异和冲突也成为了推进英国空气污染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一道难以跨越的障碍。
错综复杂的利益之争直接影响了空气污染治理的效果。1956年、1957年和1962年,伦敦城又连续发生多次严重的烟雾事件。日益恶化的环境最终逼迫伦敦和整个英国开始做出改变。
结构调整
烟雾事件造成的恶果给全英国人敲响了最响亮的警钟。尽管存在着中央和地方政府、商业企业和与环境保护、普通民众与空气污染治理等种种矛盾冲突。英国最终还是踏上了空气污染治理的艰难过程。
20世纪60年代北海油气田发现,随后步入大规模开发阶段。清洁、廉价、高效、易得的天然气和石油迅速取代了煤炭在英国的地位。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能源结构开始发生巨大改变。
政府开始大规模改造伦敦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并在冬季采取集中供暖。到1965年,由于天然气和燃油的应用,煤在燃料构成中的比例减少为27%(1980年进一步减少到5%,而且还仅限于远郊区工厂使用),电和清洁气体燃料占24.5%(至1980年提高到51%),油为43%(1980年为41%)。
而现在,煤炭在英国早已不复当年“一家独大”的气势。煤炭消费量大幅度减少,油气比重上升。取暖和发电的燃煤机组逐渐在环保政策和经济效益的双重作用下不断被淘汰。今天的英国,煤炭占到整个英国能源消费从巅峰期的超过60%下降到了不到20%。
应对雾霾,伦敦市也采取了最直接的办法:工厂外迁。英国是最早产生并实践卫星城概念的国家。早在1898年,英国人霍华德就在自己的书中提出了类似卫星城的概念。20世纪初,英国率先开始建设卫星城。
伦敦没有生硬的直接将工厂迁出伦敦市区的范围,而是为了配合工厂的外迁,建设了配套的生活基础设施,开始了卫星城的大规模建设。伦敦在40年代末建设的8座新城的基础上,于60年代末在城市以北地区又兴建了彼得伯勒,在西北地区兴建了米尔顿凯恩斯、北安普顿等3座新城。这3座新城距伦敦市中心的距离80至133公里不等。
自1967年起,伦敦市区工业用地开始减少,至1974年市区共迁出2.4万个劳动岗位,以后又迁出4.2万个。与此同时,新城企业却由原来的823家,增加到2558家,新城的人口总数也由原来的45万增至100多万。
现在的伦敦由中心的伦敦市,以及内伦敦和外伦敦共同组成。所有的工厂都已经迁离核心的伦敦市和周围的几个属于内伦敦的区域。那些空置下来的廉价厂房,吸引了许多落魄的艺术家们。臭名昭著的伦敦东区更是2012伦敦奥运会场馆建设的主要区域。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严重的烟雾事件再也没有发生在伦敦城中。从毒雾缭绕到蓝天白云,伦敦上空笼罩了一百多年的“阴影”终告消散。一个世纪的法律建设、利益重重的冲突博弈、经济效益的“无形之手”、大刀阔斧的城市规划,伦敦最终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时至今日,伦敦早已不是柯南道尔爵士笔下那个充满犯罪的“雾都”。如今,只有偶尔在冬季或初春的早晨才能看到一层薄薄的白色雾霭。湛蓝的天空甚至让人怀疑“雾都”之名是否是古人太言过其实。然而泛黄的黑白照片和专为19世纪末伦敦而创的“smog”一词却始终都在警醒着后人。